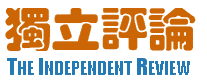为老共着急那样。 刘刚可能也要步老王后尘。
我也一向认为,八九学运诸领袖中,刘刚是最smart的一位。但是后来中共对他的洗脑太厉害,整天跟他说些贬低异议人士的坏话,使得他对异议者的观感有很大的片面性,有段时间几乎是国内出来一个就要攻击一个,指责人家是中共放出的特务,等等。
这就是我有时忍不住要向刘王开火的原因。
从刘刚这篇话的读出的意思(也许不是他心中的原意),好像八九参加学运的同学,都没什么民主的诉求,只是为了逃避学业压力而参加一场狂欢,只有刘刚才是又有民主理念,又有清醒的头脑、
"大多数学生在游行的时候都只是将那当成是一种狂欢节,这其中甚至很少有人认为这会给中国带来民主自由,也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是民主斗士。"
"8964期间的学生没什么组织,人们也没什么具体的目标和政治诉求,甚至没什么利益动机。"
事实上,参加学运的学生有非常明确的民主诉求,这就是要有真正代表自己的学生组织,反对让官办的学生会代表自己。 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要求当局承认高自联是合法的学生组织。这其实就是要求结社自由和选举代表的权利,以任何标准看,这都是最正宗的民主诉求。
学生提出的“反贪官,反官倒”等当然也是民主诉求,虽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争取民心,掩护自己的安全。学生们提得最迫切,最明确的诉求是要求当局承认学运不是“动乱”,而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这当然是为了希望免遭秋后算账的政治迫害。这也是为了保障自己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权利,本身也是一种民主诉求。
至于学生六四之前坚守广场,未能撤退,原因当然更不是贪恋狂欢,害怕读书。我过去就此话题与不少人交流过。这次为了节省时间,不多写了,就挑了一篇,是2009年与山东大学的六四学领潘强的交流附在这里:
---------------------
潘兄:
六四以来,有关六四的争议一直没有停过,看来也不会停。六四是一场失败的民主运动,它的失败使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迟了至少20年,这一点,大概争议已经不多了,所争议的是,为什么败了。这个问题是许多其他争议问题的中心,从这个问题又牵扯出其他许多问题,带出很多情绪,例如谁应该为失败负责,台前台后的策划者有没有道德问题,等等。许多问题一个套一个,以致成了一团讲不清,理还乱的乱麻。
要跳出这团乱麻,还得从认识论方法论说起,否则永远理不出头。(这可以推广到一切复杂问题的讨论,当你觉得问题说不清时,难以取得共识时,就应该检查我们的思维工具,检查问题本身是够恰当,)人们在讨论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时,常常也象讨论物理化学问题一样,要讨论因果律,即原因和结果。而这些讨论,一般也是为了指导实践,或者用杜威的话说是为了对付生活环境的挑战。因而在讨论因果关系时,实际上受到了手段和目的关系的影响,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说,讨论因果关系,实际上是在讨论手段和目的。
当人们讨论物理化学问题时,通常讨论的各方都会有相同的角度,那就是一个客观,旁观的角度,大家也有相同的目的,要解决共同关心的人类科研问题,因此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取得共识,比较不容易动激烈情绪。但是在讨论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时,讨论者往往有一种参与者的角度,而且是动机各不相同的参与者。于是问题就复杂了,常常是谁也不服谁,达不到一致结果,最后不了了之。在民主社会里,人们也习惯了怀疑主义的思维,认识到这种没有统一观点的场面是正常现象,因此也就心安理得了。凡事听了一种说法后,一般都希望听到至少另一种不同说法,然后,如果必要的话,就像个法官一样,根据自己的良心和一定的Discretion,来决定取舍;如果没必要取舍,就将各种说法存而不论,无限期延庭了。 但是像我们中国人,还没有习惯这种怀疑主义思维,因而执直地要争出个一致结果来,于是就永远吵个不休。(我不是反对争论,而是说,要准备争不出结果,要有平常心,不要愤愤然。)
有了这些思想准备后,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问题。首先我还是要举个物理问题的例子,来说明我们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所谓怀疑主义,就是认识到人类理智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要烧开一壶水,但是没有成功,请问这是为什么?
通常,我们总是说,水没烧开是因为温度不够,或者进一步说,是因为火力不足或时间不够,如果加大火力,或者多烧一会儿,让水到达一定的温度,水就会开。当然,原因后面还可以有原因,例如火力不够可以是燃料不够,或氧气不足等等,这种原因的原因,是大家都熟悉的范畴,在此不必多论。我要提请注意的是,这里还可以存在着常人不大提起的“原因”,例如气压问题,如果气压低一点,即使水没到100度,也会开。或者说,这水里有杂质,所以到了100度,水也没开。所以气压或者杂质,也可以说是水没有开的“原因”。如果你不怕无聊的话,我还可以举出其他“原因”,例如,水的分子量,如果再小一点,水大概也会开了。或者水分子之间的场力,什么强力弱力范氏力,都可以说成是水没开的“原因”。加上原因后面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对“水未烧开”这一结果,可以找出无限多个“原因”,这些原因,在物理上都没有错!
可是我们一般只会说,水没有开的原因是温度不够,温度不够是因为火力不够或时间不够。为什么不提其他“原因”呢?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在物理学上不对,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在生活中没有意义!”It does not make a sense.” 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一般条件下,你只能控制火力和时间,对其他原因,你无法操作,无法改变, “It is out of your reach。” 既然和手段与目的不沾边,那就没了意义。
由此可见,象“水为什么”没开这样的简单问题,可以找到的原因也是无穷多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人类理智的主要工具---因果律,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不得不依靠因果律来思维,来总结经验教训,但是必须知道,原因和结果不是绝对的,不是纯客观的,因果律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强制认识的主体主观地做出一定的取舍,而不能穷尽客体的一切方面。这也就是人类理智的局限性。所以说,人类一思维,上帝就发笑。
好了,我不是基督徒,哪怕上帝先生笑话,我也只好继续分析我们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八九民运的问题上来了。对于六四中为什么民主运动失败了,这一点,可以找出的原因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无穷多的,或曰学生未能见好就收焉,或曰赵紫阳未能登高一呼焉,或曰民运方未能决心推翻中共焉,或曰知识分子没能负责焉,或曰没有组织纲领,或曰没有中产阶级,等等,等等,so on and so on. 差不多每一个原因,背后都有着不同的对于目的和手段的考虑。
这些原因都不能说是错的,但问题是,哪一个,或几个是有意义的?Does it make sense? 我认为,这就要看各人的角度,那些是你,或者你所设身考虑的角色,可以操控的?这就像做买卖或炒股票一样,买卖做砸了,你固然可以找出许多客观原因,或是你所无法改变的原因,但是除非你是不想再干了,既然还要干,你就要找找自己的原因,或者是自己所能操控的原因。因为你没法改变别人,你只能改变自己。如果你只找人家原因不找自己原因,那么你下一次干,你还得失败。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变,没法变。
那么我作我的回忆及评论八九的时候,我的角度或角色是什么呢?我从1984年开始是个中国民联成员。我只能从一个民运人士的角度,或者是海外民运的角度,来总结经验。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赵紫阳登高一呼上,因为这是我们所不能操控的因素,除非你有力量或有本事象辛亥年那样, 用枪逼着赵当黎元洪。
在我看来,当时并不存在着推翻政府,改朝换代的条件,绝大多数参与者也并没有这样的野心。赵当然也不可能跳出来与中共决裂,或与邓小平决裂。大多数坚持在广场上的人,其思路是希望能迫使邓小平或中共决策者改变主意,在民众压力下抛弃李鹏,宣布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 (当年的“爱国”似乎还很光荣)。或者是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共产党教育,来感动军队,反戈一击。
今天谈起来,似乎当时军队反击,推翻政府都是可能的,这个我当然不同意,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The point is, 我们是不是可以为着这样的可能性去大赌一场,以千百条人命去孤注一掷?就如同你搞投资,不能只考虑收益不考虑成本,只考虑可能的利润不考虑血本无归的风险,不能只希望成功而不考虑失败,尤其是,当你要去用别人的成本,借来的资金。所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撤退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保险系数最高的,因为中国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你就要考虑保存实力,以待将来。
以上是回答您的关于赵紫阳的六四表现,以及与此相关的,学生该不该撤的问题。这个回答当然远未答透,但是现在只能先告一段落,因为我们立刻就要讨论由此牵出的另一问题,学生是不是撤得了。(我说过我们是在理一团乱麻。)
诚如潘兄所言,“以学生群体当时的知识面,社会经验,加上无民主传统而临时揭竿而起的学生组织对全局的驾驭能力非常有限,没有一个学生或学生组织在当时可以让这种短期的,自发的大规模学生运动收发自如。”其实,我还要加上周围环境的舆论误导,尤其是海外和台湾舆论的表现,再加上中共顽固派处心积虑地非要将学生逼反,以便全歼,都使得学生撤不了。 赵紫阳有赵紫阳的局限和无奈,学生也有学生的局限和无奈,苛求任何一方都有失公正,即使在逻辑上不能证明是错,至少在实际生活中没有意义,does not make a sense.
但是我的角度也不是学生一方,而是海外民运一方,我们当时可以,或者说,应该做些什么。这就是我的回忆和我的总结中的角度或角色。 在王炳章时代的中国之春和海外民运,我们的宗旨是很清楚的,我们并没有谋求推翻现政权,我们只是追求在中国出现合法的反对党和压力团体,以对执政者实行真正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一点,也许现在让有些人看不上眼,但是当时至少表面上是无争议的盟内共识。
如果坚持这一点宗旨,那么在八九民运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学生已经建立了学自联等团体,当务之急是怎样让他合法或半合法的生存下去,以为来日张本。民主党派和官办报刊,已经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当务之急是怎样让他们有条件保持下去,可持续发展。这些都需要让八九民运和平收场,避免流血结局,更何况还有千万条人命。
民联当时已经有所嬗变,但我因为与之隔离,无所体会,所以依然假设它路线未变。所以我当时极力希望民联能发出学生撤退的呼吁。这里当然有本位主义的考虑,认为如果能说动学生,对民联积累credit有益,表明民联是一个负责任的团体,对将来合法登陆有利。即使不成功,将来在政治上也比较主动,至少是少挨些骂。但是更多的,还是从大局考虑。
当时胡平当家的民联,未能发出这样的呼吁,是我的千古遗憾,这些都不必说了,以下只能猜测如果民联发出撤退呼吁,是否能为学生所接受的问题。
恰如潘兄提到的,当时在广场上,撤与不撤的意见几乎是势均力敌,不断地有人游说要撤,又不断的有人打气说要留。这就是普利高津混纯学理论所说的高度激发态,其特点是,任何一个平时不起眼的因素,此时都有可能打破力量的平衡,牵动大局走向某一方向。这就叫做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我在《我看八九》一问中说过: 必须指出,在八九民运中不乏理智冷静之士,他们审慎地认识到形势的凶险,想方设法避免流血的前途,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万润南在四通召集学运领袖开会,提出适时进行“胜利大凯旋”的主张,一度被学运领袖接受,后又推翻。吾尔开希和柴玲都曾因为主张适时撤离而遭罢免。运动后期几乎成了比激进的比赛,主张暂时退让的人立刻受到威胁,被指为“学贼”或“内奸”,而绝无内奸之嫌的海外民运组织又未能发挥正确作用,结果坐失良机,局势终于无救。这就反映出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的民主素质不够成熟的问题。
在我对六四的回忆中也说:“当时广场上的学生似乎是撤兵的意见都听不进,谁说撤谁就是孬种,软骨头或学贼等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民主的泛道德主义:遇到一个意见常常不是就事论事地讲道理,分析其合理性,而是追究提意见者的立场,态度,道德,动机等等,以臆想的动机否定合理意见,)但是对海外舆论还是相当敏感的,美国之音,台湾电台,香港报刊都是人人(包括学生)天天渴望听和看的东西。可惜的是海外华人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都是支持广场上的学生坚持下去,直到李鹏下台的。 这里除了隔岸观火的隔膜外,亦很难排除不同利益机制上的原因,言之令人心痛。 但是世界舆论是相对理性的,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都呼吁中国政府和学生双方都采取克制的态度,协商解决纠纷。 我想,如果民联能发出谈判的呼吁,必能得到世界舆论的欣赏和共鸣,从而影响海外华人的舆论,共同设法促成学生与政府的和平解决。 学生恐怕不会认为当时的海外舆论,尤其是民联,有助共,学贼,或软骨头的嫌疑。
此外,我还提到我当时的其他理由:正如国外的盟友把民联估计太低一样,我在国内把民联估计太高。在我心中,民联的形象还没有分裂,还是她初创时那生气勃勃的模样。 国内人民并不太相信通过中共媒体传进来的有关民联的负面消息。 袁木与学生对话时训斥说,你们的行动使人痛心,只有民联看了才会高兴;这话确实使我很高兴。 《参考消息》上 “民联份子王炳章,汤光中企图回国插手学运”的报导也给人一定鼓舞。 胡平,陈军等人致学生的信被抄出来贴在北大三角地。 胡平这位《论言论自由》的作者在北京学生心中的份量更不可小看。
我忘不了,1989年5月19日晚上,我奉胡平之命,代表民联去见上海学生。当我在外滩向上海学生说出,我们民联希望你们现在无条件撤回学校的时候,有五六只手伸过来和我握手。当然,上海和北京民情不同,北京的情况要复杂的多,不能简单推论。
潘兄也提到,“刘晓波等四君子在“六。四”天安门绝境中让绝大部分学生安全撤离,知识分子对不太成熟的年轻学生影响力可见一斑。“ 我要加一句,刘的海龟身份,侯的台湾身份,在当时的学生看来,都减少了其“学贼”的嫌疑。可惜四君子也动手太晚了。他们出面的时候,谈判撤退的时机已经基本丧失了。所以,当时地位有利得多的民联,没有出面呼吁,实在是太可惜了。都说历史没有假设,如今说什么都好象白搭,实在无奈。
综上所述,我在我的回忆和反思中,我的批评对象始终是海外民运和海外舆论,而非针对广场的学生,更不是针对个别学运领袖。在《我看八九》一文中我说过: “在此要说明我并不想指责战斗在八九民运斗争前列的青年学生,我对他们只有敬佩,他们已经为中国的民主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们才二十岁上下,又是在铁幕中接受全部教育,有什么不成熟处是理所当然的。我在二十来岁时比他们傻得多啦!让他们在自由世界中假以时日,一定会很快成熟起来,多半会比我辈更有出息。其实当时一些海外人士不见得就比学运领袖更清醒,而现在却在过多地指责学生。在我看来倒是些老民运人士和海外学人需要更多的反省。”
好了,潘兄,我现在只能先“商榷”这些,我知道许多问题还没说透,以后再交流吧。
祝好!
Wei Yang
我也一向认为,八九学运诸领袖中,刘刚是最smart的一位。但是后来中共对他的洗脑太厉害,整天跟他说些贬低异议人士的坏话,使得他对异议者的观感有很大的片面性,有段时间几乎是国内出来一个就要攻击一个,指责人家是中共放出的特务,等等。
这就是我有时忍不住要向刘王开火的原因。
从刘刚这篇话的读出的意思(也许不是他心中的原意),好像八九参加学运的同学,都没什么民主的诉求,只是为了逃避学业压力而参加一场狂欢,只有刘刚才是又有民主理念,又有清醒的头脑、
"大多数学生在游行的时候都只是将那当成是一种狂欢节,这其中甚至很少有人认为这会给中国带来民主自由,也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是民主斗士。"
"8964期间的学生没什么组织,人们也没什么具体的目标和政治诉求,甚至没什么利益动机。"
事实上,参加学运的学生有非常明确的民主诉求,这就是要有真正代表自己的学生组织,反对让官办的学生会代表自己。 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要求当局承认高自联是合法的学生组织。这其实就是要求结社自由和选举代表的权利,以任何标准看,这都是最正宗的民主诉求。
学生提出的“反贪官,反官倒”等当然也是民主诉求,虽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争取民心,掩护自己的安全。学生们提得最迫切,最明确的诉求是要求当局承认学运不是“动乱”,而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这当然是为了希望免遭秋后算账的政治迫害。这也是为了保障自己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权利,本身也是一种民主诉求。
至于学生六四之前坚守广场,未能撤退,原因当然更不是贪恋狂欢,害怕读书。我过去就此话题与不少人交流过。这次为了节省时间,不多写了,就挑了一篇,是2009年与山东大学的六四学领潘强的交流附在这里:
---------------------
潘兄:
六四以来,有关六四的争议一直没有停过,看来也不会停。六四是一场失败的民主运动,它的失败使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迟了至少20年,这一点,大概争议已经不多了,所争议的是,为什么败了。这个问题是许多其他争议问题的中心,从这个问题又牵扯出其他许多问题,带出很多情绪,例如谁应该为失败负责,台前台后的策划者有没有道德问题,等等。许多问题一个套一个,以致成了一团讲不清,理还乱的乱麻。
要跳出这团乱麻,还得从认识论方法论说起,否则永远理不出头。(这可以推广到一切复杂问题的讨论,当你觉得问题说不清时,难以取得共识时,就应该检查我们的思维工具,检查问题本身是够恰当,)人们在讨论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时,常常也象讨论物理化学问题一样,要讨论因果律,即原因和结果。而这些讨论,一般也是为了指导实践,或者用杜威的话说是为了对付生活环境的挑战。因而在讨论因果关系时,实际上受到了手段和目的关系的影响,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说,讨论因果关系,实际上是在讨论手段和目的。
当人们讨论物理化学问题时,通常讨论的各方都会有相同的角度,那就是一个客观,旁观的角度,大家也有相同的目的,要解决共同关心的人类科研问题,因此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取得共识,比较不容易动激烈情绪。但是在讨论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时,讨论者往往有一种参与者的角度,而且是动机各不相同的参与者。于是问题就复杂了,常常是谁也不服谁,达不到一致结果,最后不了了之。在民主社会里,人们也习惯了怀疑主义的思维,认识到这种没有统一观点的场面是正常现象,因此也就心安理得了。凡事听了一种说法后,一般都希望听到至少另一种不同说法,然后,如果必要的话,就像个法官一样,根据自己的良心和一定的Discretion,来决定取舍;如果没必要取舍,就将各种说法存而不论,无限期延庭了。 但是像我们中国人,还没有习惯这种怀疑主义思维,因而执直地要争出个一致结果来,于是就永远吵个不休。(我不是反对争论,而是说,要准备争不出结果,要有平常心,不要愤愤然。)
有了这些思想准备后,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问题。首先我还是要举个物理问题的例子,来说明我们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所谓怀疑主义,就是认识到人类理智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要烧开一壶水,但是没有成功,请问这是为什么?
通常,我们总是说,水没烧开是因为温度不够,或者进一步说,是因为火力不足或时间不够,如果加大火力,或者多烧一会儿,让水到达一定的温度,水就会开。当然,原因后面还可以有原因,例如火力不够可以是燃料不够,或氧气不足等等,这种原因的原因,是大家都熟悉的范畴,在此不必多论。我要提请注意的是,这里还可以存在着常人不大提起的“原因”,例如气压问题,如果气压低一点,即使水没到100度,也会开。或者说,这水里有杂质,所以到了100度,水也没开。所以气压或者杂质,也可以说是水没有开的“原因”。如果你不怕无聊的话,我还可以举出其他“原因”,例如,水的分子量,如果再小一点,水大概也会开了。或者水分子之间的场力,什么强力弱力范氏力,都可以说成是水没开的“原因”。加上原因后面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对“水未烧开”这一结果,可以找出无限多个“原因”,这些原因,在物理上都没有错!
可是我们一般只会说,水没有开的原因是温度不够,温度不够是因为火力不够或时间不够。为什么不提其他“原因”呢?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在物理学上不对,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在生活中没有意义!”It does not make a sense.” 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一般条件下,你只能控制火力和时间,对其他原因,你无法操作,无法改变, “It is out of your reach。” 既然和手段与目的不沾边,那就没了意义。
由此可见,象“水为什么”没开这样的简单问题,可以找到的原因也是无穷多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人类理智的主要工具---因果律,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不得不依靠因果律来思维,来总结经验教训,但是必须知道,原因和结果不是绝对的,不是纯客观的,因果律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强制认识的主体主观地做出一定的取舍,而不能穷尽客体的一切方面。这也就是人类理智的局限性。所以说,人类一思维,上帝就发笑。
好了,我不是基督徒,哪怕上帝先生笑话,我也只好继续分析我们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八九民运的问题上来了。对于六四中为什么民主运动失败了,这一点,可以找出的原因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无穷多的,或曰学生未能见好就收焉,或曰赵紫阳未能登高一呼焉,或曰民运方未能决心推翻中共焉,或曰知识分子没能负责焉,或曰没有组织纲领,或曰没有中产阶级,等等,等等,so on and so on. 差不多每一个原因,背后都有着不同的对于目的和手段的考虑。
这些原因都不能说是错的,但问题是,哪一个,或几个是有意义的?Does it make sense? 我认为,这就要看各人的角度,那些是你,或者你所设身考虑的角色,可以操控的?这就像做买卖或炒股票一样,买卖做砸了,你固然可以找出许多客观原因,或是你所无法改变的原因,但是除非你是不想再干了,既然还要干,你就要找找自己的原因,或者是自己所能操控的原因。因为你没法改变别人,你只能改变自己。如果你只找人家原因不找自己原因,那么你下一次干,你还得失败。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变,没法变。
那么我作我的回忆及评论八九的时候,我的角度或角色是什么呢?我从1984年开始是个中国民联成员。我只能从一个民运人士的角度,或者是海外民运的角度,来总结经验。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赵紫阳登高一呼上,因为这是我们所不能操控的因素,除非你有力量或有本事象辛亥年那样, 用枪逼着赵当黎元洪。
在我看来,当时并不存在着推翻政府,改朝换代的条件,绝大多数参与者也并没有这样的野心。赵当然也不可能跳出来与中共决裂,或与邓小平决裂。大多数坚持在广场上的人,其思路是希望能迫使邓小平或中共决策者改变主意,在民众压力下抛弃李鹏,宣布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 (当年的“爱国”似乎还很光荣)。或者是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共产党教育,来感动军队,反戈一击。
今天谈起来,似乎当时军队反击,推翻政府都是可能的,这个我当然不同意,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The point is, 我们是不是可以为着这样的可能性去大赌一场,以千百条人命去孤注一掷?就如同你搞投资,不能只考虑收益不考虑成本,只考虑可能的利润不考虑血本无归的风险,不能只希望成功而不考虑失败,尤其是,当你要去用别人的成本,借来的资金。所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撤退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保险系数最高的,因为中国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你就要考虑保存实力,以待将来。
以上是回答您的关于赵紫阳的六四表现,以及与此相关的,学生该不该撤的问题。这个回答当然远未答透,但是现在只能先告一段落,因为我们立刻就要讨论由此牵出的另一问题,学生是不是撤得了。(我说过我们是在理一团乱麻。)
诚如潘兄所言,“以学生群体当时的知识面,社会经验,加上无民主传统而临时揭竿而起的学生组织对全局的驾驭能力非常有限,没有一个学生或学生组织在当时可以让这种短期的,自发的大规模学生运动收发自如。”其实,我还要加上周围环境的舆论误导,尤其是海外和台湾舆论的表现,再加上中共顽固派处心积虑地非要将学生逼反,以便全歼,都使得学生撤不了。 赵紫阳有赵紫阳的局限和无奈,学生也有学生的局限和无奈,苛求任何一方都有失公正,即使在逻辑上不能证明是错,至少在实际生活中没有意义,does not make a sense.
但是我的角度也不是学生一方,而是海外民运一方,我们当时可以,或者说,应该做些什么。这就是我的回忆和我的总结中的角度或角色。 在王炳章时代的中国之春和海外民运,我们的宗旨是很清楚的,我们并没有谋求推翻现政权,我们只是追求在中国出现合法的反对党和压力团体,以对执政者实行真正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一点,也许现在让有些人看不上眼,但是当时至少表面上是无争议的盟内共识。
如果坚持这一点宗旨,那么在八九民运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学生已经建立了学自联等团体,当务之急是怎样让他合法或半合法的生存下去,以为来日张本。民主党派和官办报刊,已经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当务之急是怎样让他们有条件保持下去,可持续发展。这些都需要让八九民运和平收场,避免流血结局,更何况还有千万条人命。
民联当时已经有所嬗变,但我因为与之隔离,无所体会,所以依然假设它路线未变。所以我当时极力希望民联能发出学生撤退的呼吁。这里当然有本位主义的考虑,认为如果能说动学生,对民联积累credit有益,表明民联是一个负责任的团体,对将来合法登陆有利。即使不成功,将来在政治上也比较主动,至少是少挨些骂。但是更多的,还是从大局考虑。
当时胡平当家的民联,未能发出这样的呼吁,是我的千古遗憾,这些都不必说了,以下只能猜测如果民联发出撤退呼吁,是否能为学生所接受的问题。
恰如潘兄提到的,当时在广场上,撤与不撤的意见几乎是势均力敌,不断地有人游说要撤,又不断的有人打气说要留。这就是普利高津混纯学理论所说的高度激发态,其特点是,任何一个平时不起眼的因素,此时都有可能打破力量的平衡,牵动大局走向某一方向。这就叫做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我在《我看八九》一问中说过: 必须指出,在八九民运中不乏理智冷静之士,他们审慎地认识到形势的凶险,想方设法避免流血的前途,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万润南在四通召集学运领袖开会,提出适时进行“胜利大凯旋”的主张,一度被学运领袖接受,后又推翻。吾尔开希和柴玲都曾因为主张适时撤离而遭罢免。运动后期几乎成了比激进的比赛,主张暂时退让的人立刻受到威胁,被指为“学贼”或“内奸”,而绝无内奸之嫌的海外民运组织又未能发挥正确作用,结果坐失良机,局势终于无救。这就反映出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的民主素质不够成熟的问题。
在我对六四的回忆中也说:“当时广场上的学生似乎是撤兵的意见都听不进,谁说撤谁就是孬种,软骨头或学贼等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民主的泛道德主义:遇到一个意见常常不是就事论事地讲道理,分析其合理性,而是追究提意见者的立场,态度,道德,动机等等,以臆想的动机否定合理意见,)但是对海外舆论还是相当敏感的,美国之音,台湾电台,香港报刊都是人人(包括学生)天天渴望听和看的东西。可惜的是海外华人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都是支持广场上的学生坚持下去,直到李鹏下台的。 这里除了隔岸观火的隔膜外,亦很难排除不同利益机制上的原因,言之令人心痛。 但是世界舆论是相对理性的,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都呼吁中国政府和学生双方都采取克制的态度,协商解决纠纷。 我想,如果民联能发出谈判的呼吁,必能得到世界舆论的欣赏和共鸣,从而影响海外华人的舆论,共同设法促成学生与政府的和平解决。 学生恐怕不会认为当时的海外舆论,尤其是民联,有助共,学贼,或软骨头的嫌疑。
此外,我还提到我当时的其他理由:正如国外的盟友把民联估计太低一样,我在国内把民联估计太高。在我心中,民联的形象还没有分裂,还是她初创时那生气勃勃的模样。 国内人民并不太相信通过中共媒体传进来的有关民联的负面消息。 袁木与学生对话时训斥说,你们的行动使人痛心,只有民联看了才会高兴;这话确实使我很高兴。 《参考消息》上 “民联份子王炳章,汤光中企图回国插手学运”的报导也给人一定鼓舞。 胡平,陈军等人致学生的信被抄出来贴在北大三角地。 胡平这位《论言论自由》的作者在北京学生心中的份量更不可小看。
我忘不了,1989年5月19日晚上,我奉胡平之命,代表民联去见上海学生。当我在外滩向上海学生说出,我们民联希望你们现在无条件撤回学校的时候,有五六只手伸过来和我握手。当然,上海和北京民情不同,北京的情况要复杂的多,不能简单推论。
潘兄也提到,“刘晓波等四君子在“六。四”天安门绝境中让绝大部分学生安全撤离,知识分子对不太成熟的年轻学生影响力可见一斑。“ 我要加一句,刘的海龟身份,侯的台湾身份,在当时的学生看来,都减少了其“学贼”的嫌疑。可惜四君子也动手太晚了。他们出面的时候,谈判撤退的时机已经基本丧失了。所以,当时地位有利得多的民联,没有出面呼吁,实在是太可惜了。都说历史没有假设,如今说什么都好象白搭,实在无奈。
综上所述,我在我的回忆和反思中,我的批评对象始终是海外民运和海外舆论,而非针对广场的学生,更不是针对个别学运领袖。在《我看八九》一文中我说过: “在此要说明我并不想指责战斗在八九民运斗争前列的青年学生,我对他们只有敬佩,他们已经为中国的民主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们才二十岁上下,又是在铁幕中接受全部教育,有什么不成熟处是理所当然的。我在二十来岁时比他们傻得多啦!让他们在自由世界中假以时日,一定会很快成熟起来,多半会比我辈更有出息。其实当时一些海外人士不见得就比学运领袖更清醒,而现在却在过多地指责学生。在我看来倒是些老民运人士和海外学人需要更多的反省。”
好了,潘兄,我现在只能先“商榷”这些,我知道许多问题还没说透,以后再交流吧。
祝好!
Wei Yang
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1-02-25 04: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