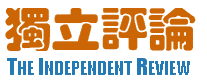�����ˣ���Һã������ǡ��۵㡱��������ޱ�����조�۵㡱��Ŀ����ͨ����Ƶ���ߣ����������ڰ��ֵ�����ʫ����������������1980����Գ�ʫ��ŵ���ʡ��䶯�й���½ʫ̳����������������������ѡΪ��ʮ��ʫ�ˡ�֮һ��2018����������˱���Ϊ�ǡ�ʫ̳ŵ����������������ʫ�����Ϊ��һ��������ٵ�����ʫ�ˡ��������ķ�֮һ���ɹ�Ѫͳ����ĸ�ǵ�һ�����Ժͺ���ͨ��������ˡ��������DZ�������ϷԺ���ٶ��ң���������÷���������ڼ���ϷԺ����ġ�1949���������ĸ�����й����������ɵ���ʿ�й���ʹ�ݹ�������������ʿ��������ֱ������Żص��������
���ߣ��ҷ������������dz��ر������ijɳ������м�ͥ����Ӱ��������ʲô�أ�
������һ�����浱Ȼ�Ҹ�����ߣ�����һ���dz��Ȱ��Ļ����ر�����ѧ������������ѧ�������һ�ֶ���֪���������Ʒ������һ�����˺�������ĸ�������Ϻ����������������Ϻ���Ӱ�������ļ�ͥ����ĸ���˾˾��������ĵ�Ӱ���ݽ�ʷ��ɽ�����ݹ�����ǧ��·�ƺ��¡������¶�ŮӢ�۴����ȣ�����Ҳ���й�����˵�����һ���ܵ��Ⱥ������Ҳ��ò���ɱ�����й�֪ʶ����֮һ������ȥ�������ӣ�ǡǡ��1955��2��23���ҳ����ĵڶ��죬�����Ҳ��ò���Ϊ����һ���ϣ���ĸ�ҵı�������Ҳ�к���̵Ĺ�����
���ߣ��Ҽǵ���˵����ʮ����ĸ��ȥ��������������һ����㡣Ϊʲô��
�������ҵ�Ȼ�ڸ�ĸ������Ѭ���£���С���Ǻ�ϲ����ѧ����������Щ���������Dz�Ҫ�������dz�������ǡǡ���ĸ��ʱ����ʵ�ϸ�˵������û��ʲô��ѧ���е�ֻ��һЩ������1976���1��7�ţ���ĸ��ͻȻ�ļ�����ȥ������Ϊ�Ǹ�ʱ�����������ǵĸ�У��ȱҽ��ҩ����ĸ��Ҳ��1976�꣬�ҵĿ���˵������͵����һ�꣬����һ����㡣����һ���������ĸ���ҶԻ����ҽ����ģ��ͱ������д�µ����֡�����Щ�����أ��ͳ��ֳ��˱���ǰ����ЩͿͿдд�Ķ�������ȫ��һ����һ�ַ���������ʵ������ĸ��ͨ����������Ҳ�����ҵڶ��ε�����ʫ�������ϵĵ�����
���ߣ���֪�����Ĵ����ܵ���ĸ��ȥ����Ӱ��dz���������Ĵ������ܵ�����Щ��ѧ����Ӱ�죿
�������ҵĴ���ij�������ϸ����Ǵ���·�߹����ġ�����������ʫ����Щʫ�˲�һ���������ڱ�����ʱ��һ������һ�ֵ��µ�СȦ�ӣ��������������˳ǣ����Ƕ�����ͽӴ���һЩ�������ִ���ѧ��Ʒ����������ʫ�ˣ�����ȵȵȡ��������ǴӴ�ѧ��ֱ��ȥ�˲�ӵĴ��ӣ�����û�л���Ӵ���Щ���������Ǿ���ղ�˵�ģ�����1976���������ֿ���˵��ʹ�����������Ժ�Խ��Խ��������һ����ٿն��ı�ֽ�ϵ��Դʣ����ҵ�����������û�й�ϵ��Ȼ�����Dz���Ǹ�������ߵģ��������ϰ����ǵ�����������Ҳ��һ���dz���Ҫ�Ŀ��á����Ǹ�����֮������ּȰ��ֺޡ�����һ�־������ӵĸ��顣ʵ���Ϻ����ҷ�����������һ���˵ĸ��飬���ǹᴩ���й�����˵������ʷ�Ļ���ͳ������ʫ�贫ͳ�ڵķdz���̵�һ�ָ��顣�����ⶼҪ���ں����ı����Ķ�˼���м䣬ȥ�ٴη�ۻ��Щ���顣
���ߣ�������1983�귢���˳�ʫŵ���ʺ䶯���й���ʫ̳����ʱ���Ŷ�ʮ���꣬����������������Լ�����һ�׳������أ�
��������ʵ����ʫ����������ɣ�������ô˵������������Ϊ�������б��ô����أ�������ȷʵ��ʫ��������������ȷʵ����Ϊ��������������һ��ת�۵㡣Ҳ�����Ǹ�ʱ����ʵ���Ѿ���ע��ֻ���ڱ���������������磬������ֻ�������˵ë��һ���˵�������Ϊ����һ��ͻȻ�����й�����һ�ַ������һ�ַ����Եġ�������ʶ��������һ�ַ��״̬����������ֻ��һ������ɵĽ����ʵ���ϣ���ʱʫ����־��һ��ͷ������˵������ʫ�����ǹ˳ǣ��Ǹ���˵��ŵ���ʱȹ˳���ʲô����Ϊ����ͻȻ����������ʫ�裬�Ѿ�ԶԶ����������һ��С��С��ʽ�ġ������绨ѩ�������ϵģ����˹���˵�質���������ɡ�ͬʱ��1983����Ϊ������������Ⱦ�˶���Ҳ���������ʫ�����е�����һ����ν�������˶���ʵ��������һ����������壬��Ϊ����ͻȻ�������Ǹ�ʱ����һ��û��ë��ë��˼���ٴλ��������Ǹ�ʱ��ʼ�����Ѿ���ȫ����ѧ������һ�����������������ڵ�һ�ֱ���������ת����һ�����ĵġ������ҵ�һ���ʻ�����ѯ��������ɴ����������ˣ����й���ͬ��ʫ����ȣ������������������ʷ��ĵ�ʵ�����Գ���ͬ�Ĵ������ԡ���������Ϊ1986�����ġ�����ʫѡ������¼���������������˳ǡ����á���������λʫ�˵���Ʒ�������ձ鱻��Ϊ���й�����ʫ�ɵĴ�������֮һ��
���ߣ��ղ����ᵽ����ʫ����֪��80������ͱ����˳����û��н��ӣ�����Ϊ���й���������ɴ���ʫ�ˡ�Ϊʲô������ʫ����������������ʫ�ɵ�ʱ��Ӱ���أ�
�����������ʵ����Ҫ˵����ʫ����������Ϊһ�����ı���ʡ���Ϊ�ղ���˵�ˣ��Ǹ�ʱ�����е��й����ﶼ��һ���������Ҳ����˵��ֽ�ϵ���Щ�ʣ�ѧ��һ����»��壬�����ǹٷ�������Ҳ�ã�����һ�����йٷ���һЩ���Է�ʽҲ�ã��������������Ե��»��塣����������ϣ�ʵ������Ϊ������˵��������Ժ��й���ʫ�贫ͳ��Ҳ�ͻ������ĺ�����û�й�ϵ�ġ���ô��ν������ʫ����ʫ���أ���ʵ�ʼ�ɵĻ�����Ƿ���ʫ��������˵�ģ������Լ���������ԡ�Ҳ����˵������һ��ʼ��������������Щ�ٴ�յ�����������������������ʱ���������ר������ʲôΨ���֤����������Щ��������ġ�������Ҳû�����ݵĴʶ�����ʫ�裬�ص�����������������ִʻ㡣̫����������ҹ�������������������������ذ��ȵȵȵȡ�������Ϊ���ǻص�������һ���˻������������Ǹ�ϰ����˵������������������أ�����������ˡ������һ���˵����������һ���������Եľٶ���ʵ����Ҳ��һ�ֿ����ԣ������ô��������ԣ����DZ��������ִ��˵����ĵĸ����ԣ�����������Դ��ˡ�ʵ����Ҳ�������ʫ�Լ����������������ĵ�ʫ�裬����������������һ��·��������
���ߣ��ҿ��������ڣ�ʫ�˺��ӵĴ������ᵽ�������������ܵ�����Ӱ���ر�����������������ʫ�Լ��������ı��磿
�����������Ҿ���һ����Ȼ��һ�����вŻ�������ʫ�ˣ�������˵����Ҳ���Ҽ���������Ҳ�Ĺ�������һ���dz��б�����ʫ�ˣ��������ʱ�գ��������������������˼����������̵Ļ������������ᷢչ�ó�ֵöࡣ������������Ϊʫ�˵��������У�����˵��������1989��3�·ݣ���1989��4��ѧ�����Ͻ�ͷֻ����ôһ���¡�����������˵����һֻ�й������״�һ����һֻ����һ����ǰ�ھ���������ˣ��������ڿ��������������궯������һ���������е����������ɶ�������Ϊһ�����е�������˵��������ǡǡ�Ƕ������ִ̼��ģ���Ϊ������������һ���������ˣ���Χ�Ļ��������˵�Ͷ�������ѹ�֣���Ϊ��Χ��û�ж���������������о��������������ֻ���ӻ�����ֻè�����������Χû�ж�������һ��������Ͱ���ѹ���ˡ�ʵ����������ǰ˾������˶���һ�����������ҿ��������������ġ���Ϊ�й�����˼���ϵ��������ر��ش�ġ�
���ߣ�˵���˾����ģ��ҿ�����������֮��д��һ��ʫ��1989����β��һ���ǣ�����������ͨͨ��һ�ꡣΪʲô���������ĸ�̾��
��������Ϊ������˵1989�겻��һ��ͻ���¼�����1976�꣨�ĸ�������ǿ�ʼ���ѣ���1978������ǽ���¿����1983�����������Ⱦ�Լ����ܱ�����һϵ�е������˶�������˵�����ʲ������ɻ��ȵȡ�������80�����������˶���˼��Ŀ���ѹ�ƣ�������һ���ľ���ʼ��������˶���ʼ������ײ�ġ�������ÿһ����εĵݽ�����ղ���˵������ʵ��ʷ�Ļ��������ң�����һ��һ����εĽ��룬ʵ���϶��ڲ�ͣ�ظ�������ע���µ�˼�������������µ������������һ���һ��ε������ĵݽ�������1988����������Ѿ��о��������ﲼ���˻�ҩζ��1988��Ĵ���������ίԱ��������ȥ����һ���ʱ��ʵ������Ҳ�����dz����Ҵ���ʫ�˾��ֲ�����һ�꣬ʵ���ϣ����ǣ��Ѿ���������ظе�������һ���Ƚ��ķ籩��������˵����һ��һϵ�й��̵ı�Ȼ�����������ڱ����Ļ���Ҳ�϶��ڹ㳡�ϣ����ǵ�ȫ���綼��Ϊ֮��Ϊ֮������ʱ����ʱ������������ʵ����������һ�����ʡ���˵������ǰ��찲�ŵ��������һ�ο���������һ����ɱ����һ�ο����Ĵ��ģ�������Ļ�����ô���Ƕ�֮ǰ������Щ���ߵ����ѵļ������Ķ��أ����������Щ���ᣬֻ������һ��һ�εس�ˢ�����Ƕ������ļ���Ļ�����ô˭���ܱ�֤��������ᣬ������Ϊδ�����µ�������һ�����أ���������������ͨͨ��һ�꣬ʵ�����Ұ�������ʴ�һ�����ڵ���ѯ��ת�Ƶ������Լ�ת�Ƶ��������ڲ������������ʵ��1989��ֻ�����������м������ͨͨ��һ��Ļ�����ô���������������������ԣ�����һ�ֳ�̬���������Ե���������ʵ�����ڽ����������ͨͨ��һ�꣬�Ѿ���÷dz���ͨ��
���ߣ��ղ����ᵽ�Ҵ��ߣ��ҿ�����˵�찲����ɱ֮���������е���Ʒ���������ڹ��ڻ��ǹ���д�ģ���ֻ�ܱ���Ϊ���Ҵ�����ѧ��Ϊʲô�أ�
��������Ϊ����88��������һ������ʱ��������ʫ��������һ�������ʱ������Ҵ��߸����ָ����һ�־����ϵ��Ҵ��ߣ������ܷ��ھ������Ҵ档����˭Ҳû���뵽�������dz������Ҵ���ʫ�˾��ֲ�֮��һ�꣬��ʵ������ӡ֤������ʡ������찲�ţ��¼���֮������ÿ���˶��Ʋ���ȥ�ģ������ס�Լ�д�µ�ÿһ���µľ��ӣ����Ǵ���������ġ������Ҵ������ʱ���Ѿ����ˣ���������д����һ����ͬ��㡣
�����ˣ��ϸ�����80����к��ڣ��ھ�����ʫ�豻���С�ʫ������������˺��й���½��һ����ʫ�˿�����š�Ư��������������ء���ô�������ǵ��кܶ�����½���ع���չ�����������ն������ء��������ء�
���ߣ�������̸һ�¹˳ǣ���Ϊ�ղ���Ҳ�ᵽ�˳ǡ���֪�����Ƕ�ʮ��ͷ����ʶ�ˣ�Ȼ������������֮������Ҳ�ܶࡣ�˳DZ���Ϊ��ͯ��ʫ�ˣ�����������Ľ��ȴ����˵ı����Ͳпᡣ����ο����˳ǵı����أ�
�������˳������������ʱ����������������Ϊ���ġ������ֻ���������֣���Ȼ���Ƿdz������ġ����������������ͯ���ģ�����ʵ�����Ҿ���������һ�棬Ҳ���й����һֱ�ں���һ�ֱ����ġ�����ij����������ר�Ƶ�����һ����������ʵ�����Ҿ�������Ը磬�����й�ÿ�����ܣ������ڣ��������ڵ����ַ��Ѵ��ۡ�
���ߣ�������Ϊһ��ʫ�ˣ�������ô���۹˳ǵ�ʫ�أ���Ϊ�ղ���Ҳ�ᵽ������ʫ�DZȽ����ҵıȽϸ��˵ıȽϴ����ģ����������������ȸ����������أ�
����������Ǻ�����˼�ģ���Ȼ��Ҳ���Ǻ�ϲ������ʫ�������Ǹ������ĽǶȡ�������ʮ����Ϳ���д��ʲô������˫�ۣ������������֮��ġ��������ǵ���������һֱ�������ڣ�����һ��ͯ��ʽ�ĵ������棬�����ǵ����DZ����뿪�й����һ�������ߣ����ʱ���һ��ʫ�����ĵij��ܣ�ѹ���������ļӴ���˵���Լ���1993�꣩д��ֹ֮ͣ����Ҳ���ǹ˳�����ȥ������һ�ꡣ����һ������ͨ����ֹ֮ͣ��������һ���ں����һ��ʹ�ñȽϴ�Ľṹ���������ҵ�����Ư�����飬������ʵΪһ�����ӣ����ǴӰ��������Լ�����֮�����������ڵ�Ư����ʵ������������Ư����һ���֡����ʱ����ͻȻ�е������ˣ��������ҵ������Լ�����˼��������Ļ������������ʽ�����ǻع�ͷ������ҿ��˳���1992��93֮��д��һ��ʫ���Ļ���������ʱ��ˮ��Ҳ�ã�������Ҳ�ã������Ǹ����Ծ���һ�ַdz����ҵķ����״̬����������˳Ǻ������������ĵķ���״̬������ȫһ�µģ���������DZ��������Ƭ��
���ߣ���������1993���ʱ�����������ֹ֮ͣ������ʱ��Ҳ˵������������������ڰ���ʱ�̡����Ǹղ�������˵��ʵҲ�Ǵ�ֹ֮ͣ������ʫ�������������ڰ��������˳����Dz��ǣ�
���������ں��ʼ�����Ժ����������һ�����⣬���ھͻ�˵�����д���Dz��Ǵ��й������ⷢ���ܴ�ת�䣿��һ�㶼�ش��ǡ���ʵ����ľ���ֻ�Ǹ���һ��ӡ֤���ҵ��й����飬�����Ҹղ�˵�ģ�ʵ����1983��ŵ���ʱ����е�ʱ�����Ѿ������������Ҽ�ȥ���ţ�����ƫ������������û�ؼң��������ۣ�����ұ�ץ��ȥ����������������ȫ��һ����ʵ������һ��һ���ľ�����������1985����Ѿ�����һƪ���½��غϵŶ��д���������ľ��ӣ�ֻ�е���Ϊ�Ϻ���ѡ���ʱ�����ϲſ��ܻ��������ɡ���Ҳ�����Һ�����������ʼ�����Ժ�ͣҪ����������һ�����ӡ�
�����ˣ���1988������������������δֹͣ�����������յ�����Ǩ�������Լ����ĸ�ֳ������֣����й��ָ塱������̫ƽ���ָ塱�͡�ŷ���ָ塱������ɡ���̫ƽ���ָ塱ʱ�ڵĴ���������ֹ֮ͣ������1996��ף�������ʼ������ŷ���ָ塱�Ĵ�����
�������Ǹ�ʱ��������Ư���Ѿ������������������ʽ����״̬����Ҳͬ��������һ���������ߵ�״̬���أ�ʵ���Ͼ�Խ��Խ�����ֱ���ġ���ͬ���Ҳ�ͬ���Ե���������Խ��Խ��������Խ��Խ���֣���ʵ��ͬ�ĵص㲻ͬ�Ĺ���������ͬ�����Ļ�������˵ĸ��������뾫��ĸ�����������ʵ��û����ô��IJ�ͬ�����������������ͬһ���ˣ����ǹŽ������ڱȽ���IJ�����棬���Ƕ���һ�ֻ�ϵ㡣����һ�����������ڴ�ֹ֮ͣ��֮��ʼд����һ����ʫ��ͬ��Բ��������뵽ͬ��Բ����ʣ�ʵ����������ѧ����һ��ͬ��Բ��Բ����ʫ��IJ�ͣ�ʣ������Ҷ����Զ���Ʒ������Ҳ��Ϊ����һ����ͣ����ʣ������������������滷����������ǵ�����ͬ��Բ��
�����ˣ���2014��ʼ������ǰ������Ӧ����Ϊ�㶫ʡ��ͷ��ѧ��ѧԺ����Ƹ���ڣ��л�����й������ѧ���������ؽ�������2017�꡶�Ҵ��ߡ����й���½��������Ϊ����֮һ������Ҳ�������μ��˸�����ʽ����1988���Ҵ��߾��ֲ��ݴ�ʱ��ӡ��ʫ�裬����ʮ�������·��ʽ��������������������Ҳ��һ�֡�ͬ��Բ����
���ߣ���֪��������ŷ�Ĵ�ѧҲ�̹��飬������αȽ��й��������˺�ŷ�������˶�ʫ���̬���أ�����������˶�������˵��ʫ����ζ��ʲô��
�������Ҿ����Ұ���ÿ������ʮ�����ҵ�ѧ���ɣ������������������Ҹе�δ�������Ǻܺõ�ʫ������ӡ���Щѧ���ܶ��Ǵ�ũ��ļ�ͥ���������ģ�д����Ʒ���Ҹе�����ֱ�ӵ�ͨ����ͥ���Լ�����������Դ�������бȽ���̵Ĺ�����һ��ѪԵ��ϵ��ij�������ϣ����ǿ���Ҳ���ϸ��ŵ�ʫ�������һ��Ѭ�հɡ���������������һ��ʫ��Ŀ���˵��������������Ҿ������ڹ����������ʫ�������߽Ӵ�����������˵�ʱ���Ҿ������ǿ��ܱȽ��٣����ڳ����Լ�д��������һ�������������˵��ϲ���ҾͶ����ܹ��Ķ��Ѿ������ˡ�
���ߣ��ղ���˵��һ�������Ҿ����ر���Ȥ����˵���ڽ����ʱ������м���ѧ���������÷dz��������������Ǵ�������ũ��ġ���������Ϊʲô��Щũ�����ĺ��ӣ����кܶ�������ʫ�˵�ʫ��ʫ�裬����������˸ж��أ�
��������Ϊʫ��Ҫ���������һ���㡢�����������һ���������ϡ����ʫ��ʧȥ����ϣ���ô�������Ѿ����һ�ַdz�û������Ķ����ˡ�����������Щũ������ĺ����ǣ��������ǵĸ�ĸ��ͨ���൱������Ͷ�Ҳ�ã���Ǯ�ĺã�����������ѧ�ȵȣ�����������Щũ��ʫ�ˣ��������ľ������й����ڵ������ߣ��뿪�Լ�������������һ����������˵���ڶ�ݸ�����dz����о�ҪԶ�öࡢİ���ö����ö�ĵط�ȥ��Ǯ��ʵ������Щ�ˣ����������������������������������������Щũ��ʫ�衣����������Ҵ��ߣ�ʫ�����������л���ʫ�跢������Ͷ���ʱ��ʵ�����ҷdz����ȵط��֣�����Щʫ���м䣬��һЩ��ȫİ����������ȫİ������Ʒ��������Щ��Ʒ�ֱ�������Щ������֪�����֣������ҿ����˵�һЩ��Ʒ��Ҫ���õ�λ�öද�˵ö࣬��Ϊ�����е�һ�ֻ���������Ѫ���ܵľ��飬Ȼ������Ҳһ���û�����ڷ�dz�ͼ��������ںţ�������Ѱ���Լ��������Լ��ı��﷽ʽ��������Ѿ�ȥ��������־���������˵���ڻ����ŵĹ���ţ������Щʫ����Dz����й�������ˣ�����ȫ���ж��ò����ˡ�
���ߣ��ԣ��Ҷ�������־�ģ���ˮ���ϵģ�����ٸ���Ҿ��÷dz�����
���������ܿ�ϧ��������û�и��Ҵ���Ͷ�壬���ڸ�ʿ�����˵�ʮ�ĸ�����¥��ɱ�ģ������ߡ����Ҹ��Ӹж��ģ����DZ�����ǧ�����������������װ��������Ⱥ��վ�ڻ�������ȫ�ǻ�����һ����������Щ���������������Ϊ������ѻȸ�����ģ�������ת��������ʱ������ͻȻ���������������������зdz����Ի�������������������Ϊ�����й���ѧ�м䣬����������������Ѫ������һ��������Ҳ��������Щ�������ҿ������й�ʫ����ǧ����������ͳû�жϾ��������ڼ�����ǰ�ߡ�
�����ˣ���������˵�������ʫ�裬�Ǹ���ʫѧ��ʱ����ʫ���DZ�ں��ף���ڡ��侲�������ŷ粨�ն�����硣�������������Ĺ۵㣬������ע���ڽ�Ŀ����������ޱ����л�տ����ٻᡣ
���ߣ��ҷ������������dz��ر������ijɳ������м�ͥ����Ӱ��������ʲô�أ�
������һ�����浱Ȼ�Ҹ�����ߣ�����һ���dz��Ȱ��Ļ����ر�����ѧ������������ѧ�������һ�ֶ���֪���������Ʒ������һ�����˺�������ĸ�������Ϻ����������������Ϻ���Ӱ�������ļ�ͥ����ĸ���˾˾��������ĵ�Ӱ���ݽ�ʷ��ɽ�����ݹ�����ǧ��·�ƺ��¡������¶�ŮӢ�۴����ȣ�����Ҳ���й�����˵�����һ���ܵ��Ⱥ������Ҳ��ò���ɱ�����й�֪ʶ����֮һ������ȥ�������ӣ�ǡǡ��1955��2��23���ҳ����ĵڶ��죬�����Ҳ��ò���Ϊ����һ���ϣ���ĸ�ҵı�������Ҳ�к���̵Ĺ�����
���ߣ��Ҽǵ���˵����ʮ����ĸ��ȥ��������������һ����㡣Ϊʲô��
�������ҵ�Ȼ�ڸ�ĸ������Ѭ���£���С���Ǻ�ϲ����ѧ����������Щ���������Dz�Ҫ�������dz�������ǡǡ���ĸ��ʱ����ʵ�ϸ�˵������û��ʲô��ѧ���е�ֻ��һЩ������1976���1��7�ţ���ĸ��ͻȻ�ļ�����ȥ������Ϊ�Ǹ�ʱ�����������ǵĸ�У��ȱҽ��ҩ����ĸ��Ҳ��1976�꣬�ҵĿ���˵������͵����һ�꣬����һ����㡣����һ���������ĸ���ҶԻ����ҽ����ģ��ͱ������д�µ����֡�����Щ�����أ��ͳ��ֳ��˱���ǰ����ЩͿͿдд�Ķ�������ȫ��һ����һ�ַ���������ʵ������ĸ��ͨ����������Ҳ�����ҵڶ��ε�����ʫ�������ϵĵ�����
���ߣ���֪�����Ĵ����ܵ���ĸ��ȥ����Ӱ��dz���������Ĵ������ܵ�����Щ��ѧ����Ӱ�죿
�������ҵĴ���ij�������ϸ����Ǵ���·�߹����ġ�����������ʫ����Щʫ�˲�һ���������ڱ�����ʱ��һ������һ�ֵ��µ�СȦ�ӣ��������������˳ǣ����Ƕ�����ͽӴ���һЩ�������ִ���ѧ��Ʒ����������ʫ�ˣ�����ȵȵȡ��������ǴӴ�ѧ��ֱ��ȥ�˲�ӵĴ��ӣ�����û�л���Ӵ���Щ���������Ǿ���ղ�˵�ģ�����1976���������ֿ���˵��ʹ�����������Ժ�Խ��Խ��������һ����ٿն��ı�ֽ�ϵ��Դʣ����ҵ�����������û�й�ϵ��Ȼ�����Dz���Ǹ�������ߵģ��������ϰ����ǵ�����������Ҳ��һ���dz���Ҫ�Ŀ��á����Ǹ�����֮������ּȰ��ֺޡ�����һ�־������ӵĸ��顣ʵ���Ϻ����ҷ�����������һ���˵ĸ��飬���ǹᴩ���й�����˵������ʷ�Ļ���ͳ������ʫ�贫ͳ�ڵķdz���̵�һ�ָ��顣�����ⶼҪ���ں����ı����Ķ�˼���м䣬ȥ�ٴη�ۻ��Щ���顣
���ߣ�������1983�귢���˳�ʫŵ���ʺ䶯���й���ʫ̳����ʱ���Ŷ�ʮ���꣬����������������Լ�����һ�׳������أ�
��������ʵ����ʫ����������ɣ�������ô˵������������Ϊ�������б��ô����أ�������ȷʵ��ʫ��������������ȷʵ����Ϊ��������������һ��ת�۵㡣Ҳ�����Ǹ�ʱ����ʵ���Ѿ���ע��ֻ���ڱ���������������磬������ֻ�������˵ë��һ���˵�������Ϊ����һ��ͻȻ�����й�����һ�ַ������һ�ַ����Եġ�������ʶ��������һ�ַ��״̬����������ֻ��һ������ɵĽ����ʵ���ϣ���ʱʫ����־��һ��ͷ������˵������ʫ�����ǹ˳ǣ��Ǹ���˵��ŵ���ʱȹ˳���ʲô����Ϊ����ͻȻ����������ʫ�裬�Ѿ�ԶԶ����������һ��С��С��ʽ�ġ������绨ѩ�������ϵģ����˹���˵�質���������ɡ�ͬʱ��1983����Ϊ������������Ⱦ�˶���Ҳ���������ʫ�����е�����һ����ν�������˶���ʵ��������һ����������壬��Ϊ����ͻȻ�������Ǹ�ʱ����һ��û��ë��ë��˼���ٴλ��������Ǹ�ʱ��ʼ�����Ѿ���ȫ����ѧ������һ�����������������ڵ�һ�ֱ���������ת����һ�����ĵġ������ҵ�һ���ʻ�����ѯ��������ɴ����������ˣ����й���ͬ��ʫ����ȣ������������������ʷ��ĵ�ʵ�����Գ���ͬ�Ĵ������ԡ���������Ϊ1986�����ġ�����ʫѡ������¼���������������˳ǡ����á���������λʫ�˵���Ʒ�������ձ鱻��Ϊ���й�����ʫ�ɵĴ�������֮һ��
���ߣ��ղ����ᵽ����ʫ����֪��80������ͱ����˳����û��н��ӣ�����Ϊ���й���������ɴ���ʫ�ˡ�Ϊʲô������ʫ����������������ʫ�ɵ�ʱ��Ӱ���أ�
�����������ʵ����Ҫ˵����ʫ����������Ϊһ�����ı���ʡ���Ϊ�ղ���˵�ˣ��Ǹ�ʱ�����е��й����ﶼ��һ���������Ҳ����˵��ֽ�ϵ���Щ�ʣ�ѧ��һ����»��壬�����ǹٷ�������Ҳ�ã�����һ�����йٷ���һЩ���Է�ʽҲ�ã��������������Ե��»��塣����������ϣ�ʵ������Ϊ������˵��������Ժ��й���ʫ�贫ͳ��Ҳ�ͻ������ĺ�����û�й�ϵ�ġ���ô��ν������ʫ����ʫ���أ���ʵ�ʼ�ɵĻ�����Ƿ���ʫ��������˵�ģ������Լ���������ԡ�Ҳ����˵������һ��ʼ��������������Щ�ٴ�յ�����������������������ʱ���������ר������ʲôΨ���֤����������Щ��������ġ�������Ҳû�����ݵĴʶ�����ʫ�裬�ص�����������������ִʻ㡣̫����������ҹ�������������������������ذ��ȵȵȵȡ�������Ϊ���ǻص�������һ���˻������������Ǹ�ϰ����˵������������������أ�����������ˡ������һ���˵����������һ���������Եľٶ���ʵ����Ҳ��һ�ֿ����ԣ������ô��������ԣ����DZ��������ִ��˵����ĵĸ����ԣ�����������Դ��ˡ�ʵ����Ҳ�������ʫ�Լ����������������ĵ�ʫ�裬����������������һ��·��������
���ߣ��ҿ��������ڣ�ʫ�˺��ӵĴ������ᵽ�������������ܵ�����Ӱ���ر�����������������ʫ�Լ��������ı��磿
�����������Ҿ���һ����Ȼ��һ�����вŻ�������ʫ�ˣ�������˵����Ҳ���Ҽ���������Ҳ�Ĺ�������һ���dz��б�����ʫ�ˣ��������ʱ�գ��������������������˼����������̵Ļ������������ᷢչ�ó�ֵöࡣ������������Ϊʫ�˵��������У�����˵��������1989��3�·ݣ���1989��4��ѧ�����Ͻ�ͷֻ����ôһ���¡�����������˵����һֻ�й������״�һ����һֻ����һ����ǰ�ھ���������ˣ��������ڿ��������������궯������һ���������е����������ɶ�������Ϊһ�����е�������˵��������ǡǡ�Ƕ������ִ̼��ģ���Ϊ������������һ���������ˣ���Χ�Ļ��������˵�Ͷ�������ѹ�֣���Ϊ��Χ��û�ж���������������о��������������ֻ���ӻ�����ֻè�����������Χû�ж�������һ��������Ͱ���ѹ���ˡ�ʵ����������ǰ˾������˶���һ�����������ҿ��������������ġ���Ϊ�й�����˼���ϵ��������ر��ش�ġ�
���ߣ�˵���˾����ģ��ҿ�����������֮��д��һ��ʫ��1989����β��һ���ǣ�����������ͨͨ��һ�ꡣΪʲô���������ĸ�̾��
��������Ϊ������˵1989�겻��һ��ͻ���¼�����1976�꣨�ĸ�������ǿ�ʼ���ѣ���1978������ǽ���¿����1983�����������Ⱦ�Լ����ܱ�����һϵ�е������˶�������˵�����ʲ������ɻ��ȵȡ�������80�����������˶���˼��Ŀ���ѹ�ƣ�������һ���ľ���ʼ��������˶���ʼ������ײ�ġ�������ÿһ����εĵݽ�����ղ���˵������ʵ��ʷ�Ļ��������ң�����һ��һ����εĽ��룬ʵ���϶��ڲ�ͣ�ظ�������ע���µ�˼�������������µ������������һ���һ��ε������ĵݽ�������1988����������Ѿ��о��������ﲼ���˻�ҩζ��1988��Ĵ���������ίԱ��������ȥ����һ���ʱ��ʵ������Ҳ�����dz����Ҵ���ʫ�˾��ֲ�����һ�꣬ʵ���ϣ����ǣ��Ѿ���������ظе�������һ���Ƚ��ķ籩��������˵����һ��һϵ�й��̵ı�Ȼ�����������ڱ����Ļ���Ҳ�϶��ڹ㳡�ϣ����ǵ�ȫ���綼��Ϊ֮��Ϊ֮������ʱ����ʱ������������ʵ����������һ�����ʡ���˵������ǰ��찲�ŵ��������һ�ο���������һ����ɱ����һ�ο����Ĵ��ģ�������Ļ�����ô���Ƕ�֮ǰ������Щ���ߵ����ѵļ������Ķ��أ����������Щ���ᣬֻ������һ��һ�εس�ˢ�����Ƕ������ļ���Ļ�����ô˭���ܱ�֤��������ᣬ������Ϊδ�����µ�������һ�����أ���������������ͨͨ��һ�꣬ʵ�����Ұ�������ʴ�һ�����ڵ���ѯ��ת�Ƶ������Լ�ת�Ƶ��������ڲ������������ʵ��1989��ֻ�����������м������ͨͨ��һ��Ļ�����ô���������������������ԣ�����һ�ֳ�̬���������Ե���������ʵ�����ڽ����������ͨͨ��һ�꣬�Ѿ���÷dz���ͨ��
���ߣ��ղ����ᵽ�Ҵ��ߣ��ҿ�����˵�찲����ɱ֮���������е���Ʒ���������ڹ��ڻ��ǹ���д�ģ���ֻ�ܱ���Ϊ���Ҵ�����ѧ��Ϊʲô�أ�
��������Ϊ����88��������һ������ʱ��������ʫ��������һ�������ʱ������Ҵ��߸����ָ����һ�־����ϵ��Ҵ��ߣ������ܷ��ھ������Ҵ档����˭Ҳû���뵽�������dz������Ҵ���ʫ�˾��ֲ�֮��һ�꣬��ʵ������ӡ֤������ʡ������찲�ţ��¼���֮������ÿ���˶��Ʋ���ȥ�ģ������ס�Լ�д�µ�ÿһ���µľ��ӣ����Ǵ���������ġ������Ҵ������ʱ���Ѿ����ˣ���������д����һ����ͬ��㡣
�����ˣ��ϸ�����80����к��ڣ��ھ�����ʫ�豻���С�ʫ������������˺��й���½��һ����ʫ�˿�����š�Ư��������������ء���ô�������ǵ��кܶ�����½���ع���չ�����������ն������ء��������ء�
���ߣ�������̸һ�¹˳ǣ���Ϊ�ղ���Ҳ�ᵽ�˳ǡ���֪�����Ƕ�ʮ��ͷ����ʶ�ˣ�Ȼ������������֮������Ҳ�ܶࡣ�˳DZ���Ϊ��ͯ��ʫ�ˣ�����������Ľ��ȴ����˵ı����Ͳпᡣ����ο����˳ǵı����أ�
�������˳������������ʱ����������������Ϊ���ġ������ֻ���������֣���Ȼ���Ƿdz������ġ����������������ͯ���ģ�����ʵ�����Ҿ���������һ�棬Ҳ���й����һֱ�ں���һ�ֱ����ġ�����ij����������ר�Ƶ�����һ����������ʵ�����Ҿ�������Ը磬�����й�ÿ�����ܣ������ڣ��������ڵ����ַ��Ѵ��ۡ�
���ߣ�������Ϊһ��ʫ�ˣ�������ô���۹˳ǵ�ʫ�أ���Ϊ�ղ���Ҳ�ᵽ������ʫ�DZȽ����ҵıȽϸ��˵ıȽϴ����ģ����������������ȸ����������أ�
����������Ǻ�����˼�ģ���Ȼ��Ҳ���Ǻ�ϲ������ʫ�������Ǹ������ĽǶȡ�������ʮ����Ϳ���д��ʲô������˫�ۣ������������֮��ġ��������ǵ���������һֱ�������ڣ�����һ��ͯ��ʽ�ĵ������棬�����ǵ����DZ����뿪�й����һ�������ߣ����ʱ���һ��ʫ�����ĵij��ܣ�ѹ���������ļӴ���˵���Լ���1993�꣩д��ֹ֮ͣ����Ҳ���ǹ˳�����ȥ������һ�ꡣ����һ������ͨ����ֹ֮ͣ��������һ���ں����һ��ʹ�ñȽϴ�Ľṹ���������ҵ�����Ư�����飬������ʵΪһ�����ӣ����ǴӰ��������Լ�����֮�����������ڵ�Ư����ʵ������������Ư����һ���֡����ʱ����ͻȻ�е������ˣ��������ҵ������Լ�����˼��������Ļ������������ʽ�����ǻع�ͷ������ҿ��˳���1992��93֮��д��һ��ʫ���Ļ���������ʱ��ˮ��Ҳ�ã�������Ҳ�ã������Ǹ����Ծ���һ�ַdz����ҵķ����״̬����������˳Ǻ������������ĵķ���״̬������ȫһ�µģ���������DZ��������Ƭ��
���ߣ���������1993���ʱ�����������ֹ֮ͣ������ʱ��Ҳ˵������������������ڰ���ʱ�̡����Ǹղ�������˵��ʵҲ�Ǵ�ֹ֮ͣ������ʫ�������������ڰ��������˳����Dz��ǣ�
���������ں��ʼ�����Ժ����������һ�����⣬���ھͻ�˵�����д���Dz��Ǵ��й������ⷢ���ܴ�ת�䣿��һ�㶼�ش��ǡ���ʵ����ľ���ֻ�Ǹ���һ��ӡ֤���ҵ��й����飬�����Ҹղ�˵�ģ�ʵ����1983��ŵ���ʱ����е�ʱ�����Ѿ������������Ҽ�ȥ���ţ�����ƫ������������û�ؼң��������ۣ�����ұ�ץ��ȥ����������������ȫ��һ����ʵ������һ��һ���ľ�����������1985����Ѿ�����һƪ���½��غϵŶ��д���������ľ��ӣ�ֻ�е���Ϊ�Ϻ���ѡ���ʱ�����ϲſ��ܻ��������ɡ���Ҳ�����Һ�����������ʼ�����Ժ�ͣҪ����������һ�����ӡ�
�����ˣ���1988������������������δֹͣ�����������յ�����Ǩ�������Լ����ĸ�ֳ������֣����й��ָ塱������̫ƽ���ָ塱�͡�ŷ���ָ塱������ɡ���̫ƽ���ָ塱ʱ�ڵĴ���������ֹ֮ͣ������1996��ף�������ʼ������ŷ���ָ塱�Ĵ�����
�������Ǹ�ʱ��������Ư���Ѿ������������������ʽ����״̬����Ҳͬ��������һ���������ߵ�״̬���أ�ʵ���Ͼ�Խ��Խ�����ֱ���ġ���ͬ���Ҳ�ͬ���Ե���������Խ��Խ��������Խ��Խ���֣���ʵ��ͬ�ĵص㲻ͬ�Ĺ���������ͬ�����Ļ�������˵ĸ��������뾫��ĸ�����������ʵ��û����ô��IJ�ͬ�����������������ͬһ���ˣ����ǹŽ������ڱȽ���IJ�����棬���Ƕ���һ�ֻ�ϵ㡣����һ�����������ڴ�ֹ֮ͣ��֮��ʼд����һ����ʫ��ͬ��Բ��������뵽ͬ��Բ����ʣ�ʵ����������ѧ����һ��ͬ��Բ��Բ����ʫ��IJ�ͣ�ʣ������Ҷ����Զ���Ʒ������Ҳ��Ϊ����һ����ͣ����ʣ������������������滷����������ǵ�����ͬ��Բ��
�����ˣ���2014��ʼ������ǰ������Ӧ����Ϊ�㶫ʡ��ͷ��ѧ��ѧԺ����Ƹ���ڣ��л�����й������ѧ���������ؽ�������2017�꡶�Ҵ��ߡ����й���½��������Ϊ����֮һ������Ҳ�������μ��˸�����ʽ����1988���Ҵ��߾��ֲ��ݴ�ʱ��ӡ��ʫ�裬����ʮ�������·��ʽ��������������������Ҳ��һ�֡�ͬ��Բ����
���ߣ���֪��������ŷ�Ĵ�ѧҲ�̹��飬������αȽ��й��������˺�ŷ�������˶�ʫ���̬���أ�����������˶�������˵��ʫ����ζ��ʲô��
�������Ҿ����Ұ���ÿ������ʮ�����ҵ�ѧ���ɣ������������������Ҹе�δ�������Ǻܺõ�ʫ������ӡ���Щѧ���ܶ��Ǵ�ũ��ļ�ͥ���������ģ�д����Ʒ���Ҹе�����ֱ�ӵ�ͨ����ͥ���Լ�����������Դ�������бȽ���̵Ĺ�����һ��ѪԵ��ϵ��ij�������ϣ����ǿ���Ҳ���ϸ��ŵ�ʫ�������һ��Ѭ�հɡ���������������һ��ʫ��Ŀ���˵��������������Ҿ������ڹ����������ʫ�������߽Ӵ�����������˵�ʱ���Ҿ������ǿ��ܱȽ��٣����ڳ����Լ�д��������һ�������������˵��ϲ���ҾͶ����ܹ��Ķ��Ѿ������ˡ�
���ߣ��ղ���˵��һ�������Ҿ����ر���Ȥ����˵���ڽ����ʱ������м���ѧ���������÷dz��������������Ǵ�������ũ��ġ���������Ϊʲô��Щũ�����ĺ��ӣ����кܶ�������ʫ�˵�ʫ��ʫ�裬����������˸ж��أ�
��������Ϊʫ��Ҫ���������һ���㡢�����������һ���������ϡ����ʫ��ʧȥ����ϣ���ô�������Ѿ����һ�ַdz�û������Ķ����ˡ�����������Щũ������ĺ����ǣ��������ǵĸ�ĸ��ͨ���൱������Ͷ�Ҳ�ã���Ǯ�ĺã�����������ѧ�ȵȣ�����������Щũ��ʫ�ˣ��������ľ������й����ڵ������ߣ��뿪�Լ�������������һ����������˵���ڶ�ݸ�����dz����о�ҪԶ�öࡢİ���ö����ö�ĵط�ȥ��Ǯ��ʵ������Щ�ˣ����������������������������������������Щũ��ʫ�衣����������Ҵ��ߣ�ʫ�����������л���ʫ�跢������Ͷ���ʱ��ʵ�����ҷdz����ȵط��֣�����Щʫ���м䣬��һЩ��ȫİ����������ȫİ������Ʒ��������Щ��Ʒ�ֱ�������Щ������֪�����֣������ҿ����˵�һЩ��Ʒ��Ҫ���õ�λ�öද�˵ö࣬��Ϊ�����е�һ�ֻ���������Ѫ���ܵľ��飬Ȼ������Ҳһ���û�����ڷ�dz�ͼ��������ںţ�������Ѱ���Լ��������Լ��ı��﷽ʽ��������Ѿ�ȥ��������־���������˵���ڻ����ŵĹ���ţ������Щʫ����Dz����й�������ˣ�����ȫ���ж��ò����ˡ�
���ߣ��ԣ��Ҷ�������־�ģ���ˮ���ϵģ�����ٸ���Ҿ��÷dz�����
���������ܿ�ϧ��������û�и��Ҵ���Ͷ�壬���ڸ�ʿ�����˵�ʮ�ĸ�����¥��ɱ�ģ������ߡ����Ҹ��Ӹж��ģ����DZ�����ǧ�����������������װ��������Ⱥ��վ�ڻ�������ȫ�ǻ�����һ����������Щ���������������Ϊ������ѻȸ�����ģ�������ת��������ʱ������ͻȻ���������������������зdz����Ի�������������������Ϊ�����й���ѧ�м䣬����������������Ѫ������һ��������Ҳ��������Щ�������ҿ������й�ʫ����ǧ����������ͳû�жϾ��������ڼ�����ǰ�ߡ�
�����ˣ���������˵�������ʫ�裬�Ǹ���ʫѧ��ʱ����ʫ���DZ�ں��ף���ڡ��侲�������ŷ粨�ն�����硣�������������Ĺ۵㣬������ע���ڽ�Ŀ����������ޱ����л�տ����ٻ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