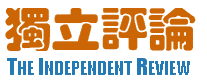��������һƪ������£�ת�����¡���
ZT�����������
��������ʰ��֮ʮһ
���ߣ��l�]��ҹ
����������������һ�N�Ļ����Ǯ�����N���˼���M���nײ��ĥ�ϵ�һ���sӰ����һ����������������ڵ��������B���Թ��ԁ����L�����������������£����еġ������Ǻ��P�I�ġ��Ļ�����Ĺ����_ʼ���e��������ˣ��������º����е�·�������϶��c�@�����Һ��@�����������vʷ�����Ĭ�������ԣ��Ƕ��ǹ��£���Ҳ���ǚvʷ��
�ڴ�ǰ�Ļؑ������e���״��ᵽ�����������@���ط��������н�������֣�Ҳ�ᵽ���ĸ��H��ĸ�H�����䌍�@һ�ҵĹ��£��h���ь�����Ҫ���ʺ��S���ܶࡣ���Գ��ˌ��T��һƪ�⣬��t�����^�a�ġ�
���������ڱ���ı��F��r�J�R�����ѣ��䌍�K��ֹ춹����������ǰl�F�˃��ˌ��r��������Ĺ�ͬ�������ڮ��r��춡���Ѫ���һ����һֱ����һ���f�����в�ͬ�汾������˼����һ�ӣ��fһ���������p�r������������ɻ��M���ӣ�����һ���]����֪���ˣ������˳���������������֮�ᣬ������D���ػ���Ȼ�����ɣ�����һ���]�����Ե��ˡ��F���҂������m�ϣ������Ҍ��Լ���˼���M���w��Փ�������p�r��Щ���£��F�ڻ�������s���¾�����ˡ�
���鸸ĸ�ļ��ڱ���������һ�������ڱ���·������·�ཻ̎����������ǰ�T꣬��ʮ��������ǂ����ӣ�겻�h��ԭ�����fַ��������ǡ������Ո��磬�����Ҿ�������Ę�Ⱥ�e������ĸ��H�н��R�£�ĸ�H���R־���������Բ���ĸ�Q֮�����������ڡ����k�������c����ġ�ʒǬ�ȹ��^�¡��ĸ��С���ͣ��������ijɡ��Ї�ؔ�Q���F�����Ո�ǰ�����������������ǰ݅����ԓ�f������@һ�c���������c�@����ͥ�ߵ����N����ԭ�������������ČW���棬�Һ���ՄՓ��Ԓ�}�h�Ƚ���ࡣ�Еr��ĸ�����Լ���ĸ�H�Ӂ�������ס������Ҳ�ǘOӑ��ϲ�g���@���ƺ����]�Ļ��������˺��҂��@Щ���^�����Ļ������˽�������Մ���g������һ��ԭ�����ϣ��к������ǷN����ͼ�������ԡ�����ҁ������^�࣬������ڱ����r��ס�������ң����ԱȄe�˸�����ij�N�Кw���H�С�
���ҵط��K�������ǷNһ��һ�d�āѾ֣��͏d�eҲ����һ���������g�Ǻ�խ�M�ģ����҂��@Щ�������ѡ��M���ᣬ�ǷN�o�εĿ��g�s�Ǻ����յġ���Ҷ���ˣ��Ƥ�ӵģ�����ĸҪؓ؟���N�ŷ����Еr߀Ҫ�����ĸ���������ӵ����Ѻÿͣ����܇�����Ҳ�ܟ��ĺ��w�N����������һ���Ŵ�ĺڰ��ҕ�C�����r߀����ϣ��֮��Еr���Ϻù�Ŀ����ĸ��ȥ�܇�����һһ���к�����Ո��ҁ����ҕ��
���_ʼ�r������ҁ����ģ�������q����һ�c�����ѣ���Ҫ�Dz���ĸ���R�����Ѻ������춲���һֱ���������������������Ҷ������ČW���Ӱ����ՄՓԒ�}��������֪����m���ǣ�����һЩ����֪���ͬ�W���ѣ�Ȼ�����ͳ��F���ϴ�W�ĸ������ѡ���ʮ������ڣ���ž���1974����1975�����ң��������ҵ����߀�Ǻ܉��ֵģ��˂�ՄՓ�Ķ���С����Ϣ��Ҳ������ʲ�N��1976������_ʼ��׃�������Ǵ����ˎ��ᣬ���������¼����F�������֏߿����@���ط�������Ҋ�C�Ї��ĸ��_�ŵĺ�������@���ط��ͳ��F�˟�Ѫ�������Ӱ���dz����[����ͬ���ˎ�����ͬ����Ϣ���ֳ����ǂ������Ϣ�����ąR���c�����Ǖr��������վ���Щ���Һ��d�^�ˡ�������S�����ѣ��Ҿ������@���r���J�R�ġ���춲����cʒǬ���^�£�����Ҳ�࣬���ă���ʒ�Y���r�ڽ�����ꠣ��ؾ��rҲ���������ҡ�ʒ�Y���r�����ֽ�ʒ�F�����L�øߴ���࣬����ʒǬ�cǰ�����ģ�ʒ�Y��ĸ�ǂ�Ӣ���ˣ�����ʒ�YҲ��һ����òͦ�εĘ��ӡ������Ը������ӣ�����Ԋ���l�����҂��@��Ⱥ�e�ǂ����Ӻ��ˡ�������_���ɞ�һ��Ԋ�ˣ��K�ڇ����W�̽��Ї��ČW�������ϛ]���x�_�����е���������܉�E�����ڵ�����߀��һ�����푛�|�ģ� ���־��Ǹߎ��ӵܣ������r�ڙz��Ժ��������춈̷����T����ͬ�҂�����һ��Ҳ��Ҋ���r�������ҵ��������B�ˡ���ԓ�v�����r�҂��@Щ�˵�˼��߀�����������ǻ�y�ģ��]���ܵ���Ҏ�ČW�g������������̫�t�������ϵ�����˼�������Ǒ{���ǰ�����x���Ы@�������`�еġ��c������푛�|��һ��Մ�r�����e�����á����a�h���ԡ����Ǿ䡸���˟o����������ԡ����r��ץ�A���Y����������Ҷ���һ�N����Ҫ��ץ������ʂ䡣�ҳ���һ�����⣬�����ゃ����������ȥ�ˣ���������ϳ�ȥ�Ҿ��鹲�a�h���[�����ڝ����R�e�@�����ɞ�һ�����x헡���
�@��Ⱥ�w��߀��һЩ�c�����ڱ��F�B꠵ı���֪�����ѣ�����һ�����B�꣬���P�S�����еģ������ϳ��˽����ڮ��r����������֡���һ����ȥ����������æ����n�����B��ȥ��վ����վ�r�����e����һ�����µġ��Y��Փ����һҊ����f���@�����Y��Փ���İ汾�DZ��^�õģ�ֵ�úúÿ��������B���@�r�ѽ����ҕ�C�S�����ˣ���֪��������һ��ϲ�g�x�����ˣ���Ҳ�W���ǂ����ӣ�ȥ�I��һ���°�ġ��Y��Փ�������ϣ�����Լ������]�Еr�g������ͨ�x�^һ�顶�Y��Փ��������B��Ҳδ�ؕ��������x�^�����鮔�r���x����ϵ�������Y��Փ����ԓ�Ǻܾ�ͨ�ģ���Ӌ���B��������Ӱ푣�����һ�������Y��Փ���汾�ĸ�Փ���F�ڿ����҂��@Щ�˶��в���������ŵĺ�Ц���顣
ͬ�r������ĵܵܽ��O����ʯ��ɽ�l늏S�����������܇�Ҳ��Ⱥ��һЩ�ˣ��ЕrҲ������������S�������ֶ�ӛ�����ˣ�ֻӛ�������ҡ���־�ʵȡ���ʮ�����һ��ؚ�F�ͅT����������Ǖrȥ�����ҵ������ˣ����Ά��ǸF���ӣ������ǡ������¡��ĺ��ӣ�һ�㶼�ǃ��ֿտ�ֻ��һ����ȥ���Ǐ�����fԒ�ͳԖ|��������r������ĸ���ϰ࣬�҂��@Щ���ĵ���������I�ˣ��͕�����ȥ�������^�Iһ���賴����Ҷ����̻��ʒ��M���ӡ�����ǰ���ٳ��^�������@�N��������С��Ӳ�������dzԵ������Ӱl�ۡ���Щ����ȥ���˶࣬���@�[����Ҫ��ģ���Dz�ĸ���°�����Ҫæµιʳ�@�����������ġ��P�ć�����ߡ���С�ӂ����Еr�ĵ���ҹ�������qδ�M����ĸ�͕�����S�����˯���ǃ���ӛ����һ������r��ʮ�킀��˯���ǃ����@Ҳ��һ�����^��
�Ǖr�ڽ���Ҹ�Մ�Փ�����rՄՓ���ľ��LJ��ҵ���������Ԟ鶼�ǿ��Ծ����µ��ˣ����Ҷ��Ƿdz��������ģ��ܿɐۣ�Ҳ�ܿ�Ц���Ă�������ٲ������҂��@�ӵ��ˡ��@Щ�����g���е�ֱ�Ӆ��c�˵����ܶ���������߄ӣ����@���r�ڵ������ˎ�ǰ�ᣬ�ǻ������@���ط���ӵĕr�⡣���Ǿ��µĖ|��̽�H���������Ϻ�ȥ���Ǖr��ȫ������ë�ɖ|���Ά��ڄ��^������hՓ�^�քݕ��l��׃�������K�]���뵽���ܿ졣���Ϻ��ᣬ�����ʮ��ʮ�����ң��ӵ�������ţ���ʾ����������׃�����ˎ��ѽ���̨���@�r�Ϻ������]�Є��o��ֱ���������R·�ϲų��F���ֈ�һ���µĕr�����@�NͻȻ���R�ˡ�
�������ٵ�����������׃�ø��ӟ��[������һЩ�����ѣ����ǻ��ཻ�Q���NС����Ϣ���������µģ������ĺ�����M�������P���ˎ͵IJ��Ϻ͈�����Ǖr�������}ӡ�C��Ҳ��֪����Һ��ğ�������ڣ����ֹ�����һ�һ퓳���������һ������Ҳ���O����ɢ�_�����^�������@�N�ֳ����О�����Ǐ��ĸ����������ġ���Щ����������Ϣ���^�ʴ_�K�õ���C�����������Ϣ����ʮ�����š���ʹ�������������Ϣ�Kδ��C����Ҍ�����Ȼ������ʡ�����Լ��M�����W�о�������ӛ���@�䌍Ҳ��ԓ��һ�����о��Ă�������W�n�}��
���ǣ����ܴ������ˎͣ������O��ľք�߀δŤ�D�����r������Ȼ̎��һ��ʮ��·�ڡ����ږ|���o�����c�������ѵĻ�ӣ���һֱ�����j�����rҲ��ֻ��ͨ�^�ż�������ӛ�î����Լ�����һƪ��Փ���¼Ľo���飬��Ӌ���ŷ�̫���]�ֲ�z�l�F���@���dz����ˡ����r���������ڱ���Ҳ�M����һЩ���O��Ļ�ӣ����磬��ͻ�����ַ��N��Ҫ��ĸ��_�ŵĴ��ֈ��f�DZ����������������ġ���֮���҂���������˼��ʂ䣬�ǂ��������Һ���Ҳ�����N�����O�z��Ҳ�S���ܶ���Ѫ�ⷽ���ּ��ϛ]�м���֮�ۡ����������˼ZƱ���X�o���飬�fһ���°lȥ�����ҹ��a�h�����[��ꠡ�
���ǣ��҂������ĵ�����K�]�г��F�F�����һ���ώֲ��ďͳ���ȫ���Ҫ��ĸ��_���γɹ��R���O��·���_ʼ�õ�Ť�D�K���������������ĸ�׃��ʹԭ���҂����еē��Ķ�һ����ȥ�ˡ��@���r��Ҷ�ͬ�@������һ�ӣ����F��һ�N�g������ľ�����ò���������@���ҵ��ֶ���һЩ�����������x�о��������ѡ�����һ���к�ƽ���Ĵ��ˣ��DZ����܌Wϵ���о������@��ȫ��һ����˼������ȫ������ČW�ߣ��mȻֻ�njW������˼���Ć��}������h��һ��ͬW��֮�ϡ���ƽ�F�������~�s���ӣ����ƺ�ՄՓ���Ά��}�^�࣬�����J������������һ���܌W�ҵĶ�λ����ԓ���҂��@��Ⱥ�w�e�ġ��W����ʽ���߀��һ�����w���������ˣ��DZ����ρ�ϵ���о�����������ρ��о��ķ������Z�W����С�Z�N�����ģ����Ժ�ʹ��Ҳ��������Ҳ�ԌW��Ӣ�Z���@������đ�Ӻܴ��˶�����Ӣ�Z�����Ŀ��Z�C������ʹ�Լ��~�������࣬Ҳǧ����Ӌȥ��ȡ�o��̓��η��g��һ�_ʼ��Ȼ�����e��ЦԒ�����r�gһ�L���e�g�������٣�����������Ǡt�����ˡ��@�N�����dz����˚J�塣�F�����������Ĵ�W�e�����Ї����}�Č��ҡ�
��������Ǖr�ѽ��γ���һ����Ӱ�����Ȧ�ӡ����r����������Ⱥ�w����F�����@�N��Ȧ�ӣ������N�ׂ������Ҳ�ܻ�����Ϥ�K������һ�µ��Єӣ���Ҫ�����Ƅ���Сƽ���³����������빤����1978���°��꣬����늈�����߅��·�ڳ��F�ˌ��T���N���ֈ�Ľ֠����@��������ȫ����ע�⡣���r���ږ|���ăȅ��e֪���@���£�ͬ�r�̨�ֲ��l����Сƽ��Ҋ�ձ������hί�T�L����ľ���r�l����ՄԒ���϶����@Щ���ֈ��ҷ��������á��@�r������o�ҁ��ţ�Մ�����ڲ߄�һ����ӡ����������ږ|���o�����c��ֻ��Մ���Լ�һЩ�O�롣�������˼��������k���������꡷�ǷN���|�Ŀ����ĸ���_�ŅȺ����@�ݿ����������r�����顶�������������|����һ���C�Ͽ������Փ���£����u������ˇ��Ʒ�ȡ�����������������c���к�ƽ���w�������푛�|�����ҡ����O��ʒ�Y����ɽ����֮�ʵȡ�
���꣬��늈�����߅�Ƕ ��l�е���ӡ������ˡ��������⣬߀�С����졷������Փ������̽����������֮�����ȣ�����@Щ������Ҫƫ�ؕr�����ٔ����ČW��Ԋ�裬������������һ���C���ԵĿ�����^���f����ߌW�g�L����һ�����oՓ����Փ����߀����ˇ��Ʒ�������ϳ˵���Ʒ������̖���з����Ĵ���������ƪ���Ѓ�ƪ�ǽ����Խ���ĹP�����ģ�һƪՓ�Y�����x��������x�^�ɣ�һƪՓ������x�Ć��}��߀��һƪ�Ǻ�ƽ������L�ġ�Փ��Փ���ɡ����@ƪ����ֱ��Ŀǰ��Ȼ�����ΌW���܌W�I���e���W����ҕ�����õġ�߀��һƪ���푛�|�������Ӱ�ČW������������n���e�����@�������������ܴ�푡������e��Ҳ�B�M���҂��Լ���˼���}�j�������Ǿ䡸���˟o��������Լ���������[�����鹝�����Ǯ����҂�������r������ĵ�˼�롣�푛�|���@���������ںܶ̕r�g���s�����ģ���ȫ�nj��Iˮƽ���f�����dz��Є������x���@�����Ϸ�ӳ�˻������@���c���ˆT�����w���|���ڶ��꣬�ɱ����Ӱ�uƬ�S�����ͳ���ġ��Ӱ������ȫ�Ŀ��l��������n���e�����K�����ĔzӋ����ֻ�����Kδ�ijɡ�
�������@Щ���ꮔ�r��Ӱ푣������������ע�����ҕ�������@Щ����Щ�������ģ����c���r������������ȫ���ģ����Ϯ��r�ߌӸĸ��ɵ�˼·�ͷ�����Ҳ���������ע����P�ա��������������ᣬ����ͨ�^�F�����λ�ֲ������j���������ӛ�������r��ҫ����f���ͺ��������@Щ���g����ӡ�������ҕ�����Õr�ΈF�����о��������R����c�������j���{�У��R���ָ���x����������꿡����������c�����j���K�H�Ե��T���������ľ�������Ҷ�Մ�ú���Ǣ�������˻�ȥ���һ�݈�棬�C�Ϸ����ˮ��r���F��������ӡ������Ќ������������u�r���^���棬�J���ˆT���|ͬ�����ױ���������ǡ������ۺģ��@�����������������ġ��R������߀�Ϊ���Ҋ�˽��飬�ɞ�oԒ��Մ�����꽻�����ã��R��谸������뾫������к����@�N��ӡ���ﲻ�����k��ȥ������Ҳ�����ֹͣ�˿����������@�N�όӺͻ��ӵ����Ի��ӣ��F�ڿ���߀���п�Ȧ���c֮̎�ġ�
�ڱ������g���ҽ��v�ˡ������������ڣ����������^��늈�����߅�ɰl�������Ƿ���ۣ����ÿ����ؓ؟һ���̿�����أ����ۣ�����ȫ����������ֿտգ�Ҳ��һ�N�ɾС���춽���ҁK�����������Ծ����O������һλ����̎����һ��Ͳ�Әǣ��܇����Ǹ������ӣ��M�M�������е��Пo���p�۾����Pע����Һ���Ҳ�����N���¡���ӡ���������������ڱ������M�еģ�ӡ�����Еr�����ҌW���俼���ǂ����g��Ҳ���ǡ�һ���߾��꡷��ƪ���������f��ɽ�����ᡣ�@�e��һ������Ȥ�IJ��������Q�������k���������ᣬ�Ǽ���ӡ�C���̎���ͳ��ˆ��}����ӡ�C�Ǐ�У��һλ���ѽ���ģ���У���õ�У�Ȇ��}�������T�l���ܣ�����У�������ã��T�l�϶�Ҫ�܁K��Ҫ���C���@�ͺ��y���f������ˡ����r�����������M����Ҫ���ږ|���T�����ڱ�߅߀��һ��С�T�������_������վ�������Ͼ����F�T�P�ϡ��Y�����҂��x��һ�����ϣ����F�T�P���ᣬ�ɂ�������ӑ����ɂ������e�������F�T�����@�Ӱ���ӡ�C�D�f�˳�ȥ��ģ��ȫȻ�����һ�ӣ��F������Ҳ��ͦ�����Ϳ�Ц�ġ��䌍������һ���e���������ƬF�������˿����ǻ��Q���x������飬߀�Ǻܶ�ġ�
�o�ɣ��ڻ������ǂ��Ҿۼ�Ȼ�����߳��������ˣ������f�����ǡ�ʡ�͵ğ������������y���f����������һ�����_ʼ�ĸ���_�ŵ���������͇�ÿһ���}�������ӣ����� ������������������1979��֮�ᣬ�mȻ��ӡ�����Dz����k�ˣ����@�����Һ���������ʼ�K�����o�p���ڶ���ͳ��F�˶�����W�ČW�����ӵط���������x�e�ĬF����ĵܵܽ��O�����������W�x�о�������һ���ڴ�ʳ��������g�������������Ұl�����f���K���х��x�˴�������ɞ鮔�r��У��һ�t��Մ������ƽҲ�ڱ�����W���х��x�˴�����������dzɹ����x�������֪��ʲ�N�]��Ϣ�ˡ�
�@Щ���鶼�����w����l���ģ����}�ǣ����Ї����r����r�£�����ܼ{���w�ƃȲ����ܷ������ɹ����P�I���oՓ��Σ��@Щ�˟��ԡ����v���ĕr���Ƕ�ʮ���q������r�ڣ��o����֮�ۣ����]�����֮�n�����ܿ죬���Մ�ِ۵�Մ�ِۣ��ɼҵijɼң��^һ���꣬��������̽�L�ģ������˃�Ů�����Ҳ���߀�������ڸ�Մ�Փ���Ҵ��º������d�������s���ˋ냺�Ŀ�����Ӗ�⺢ͯ�ĺ����ѽ��ǟ��[�Ƿ��������Ͳ�ĸҲ��æ�ò����������@���r�����˼��ҵ��ˣ��ľ����О�ģʽ���l����ijЩ׃�����҂������l�Fһ���F���Ǹ�λ��ӑ�����ţ�����ϲ��f���������e����̫ד���ɷ���ȥ�������λ�ӣ���Ҍ��@һ�cҲδ�γɷ��磬�����Ӽ��^���Ӳ�����Ҫ�ġ�����Ҫ���ǣ��@�r���Һ�����lչ��������һ�N����܉�����҂��е��S���˶��M���w�ƃȹ������@�e�����S��Ҏ�غ���Ҳ�DZ���挦��һ���F����
�ڴ�֮ǰ���������ǂ��ط������ѣ�����һֱ�����ں��Ӱ������֮�С�����������һ�����������@���r���ƺ������D�͕r�̣���ԓ��ij�N��ʽ�ġ����˶Y��������������ijЩ�r���e�и�eʽ�����r�K�]��ʲ�N�˿����뵽�@һ�c�����ǣ������{��һ�½�����ʽ����������@Щ�������ڡ�������ͣ�k�Ἧ�w���[ȥ��һ�η�ɽ�h��ʮ�ɣ��ھ��R���ϴ���һ�졣
�����҂����������T��վ�����ϵĻ�܇�����˽�����ޡ����O�ȣ�������͡��������ġ������ѡ��ֶ����ˣ�������ƽ��ʒ�Y���w���������B��ȣ���Ҷ����˳Եģ����������ε�Ұ�͡��@���ط����r��δ�_�l���[�YԴ��һ�ж���ԭ���B������ؚ�F�������ԭ���B����������Ǜ]����ՄՓ���Ҵ��£������档�Һͽ���ķ�����һ�Ԍ�����u��ʯ�K���ʂ���o���Ū�ڟᜫ��ֻ�����ț]��֪ͨ�y�I�������|������ȱ��ȼ���ľ��Ҳ�]��ú�͡���ǽ������Һ�һ���ˣ���ӛ���l�ˣ��ܿ����DŽ��B�꣩��ȥ�����r��ӑҪЩľ���ú�͡��҂��������M���f��Ҳ�S����æ�r����e�˺��٣�����Ҳ�]�P�T�����������ؼҡ������@���ط����x���DzŎ�ʮ����ʶ��������_�£���������͚������Ҹе�һ�N�Թ��ԁ���ؚ�F�����ᣬ�@Щ�|�������҂��ڳ��e��Մ�Փ�r�o�����ġ��@�����������һֱ�]�В{ȥ�����е��@��������̝Ƿ���S���˵ġ�
�Ǖr���|�T������Ҏ���ʳ�ﶼ�ܺ��Σ���߀����ĺܱM�ԣ���һ����������C�������ܴF���dz��П��[�С�����һ���߳��ǣ����O�ü����ˎ�Ԓ��������ʲ�N������һ��Сƿ�Ӄȣ�Ȼ��[��һ���f�xʽ�Ę��ӣ�ͬʒ�Y��������ѝ�ܣ�����������R���С�ʒ�Y��Сƿ���e�^�^�����O�t��������C���������ط���ؐ��ҵĵ��彻푘�������ߡ�����Ȼ���������µ��ں����İ��ǂ�Сƿ�ӷ���ˮ��Ư�ߡ����r����ڰ�߅��Ц���@һĻ�ģ������Ǹ����Ӻ���ͬ�������������đB��һ�ӣ�����߀��һЩ�J���ģ�ӣ��@������ӛ�����h�ġ����R��������ȥ�Ǵ���ӣ�Ȼ����R�뺣�ӣ�������������������룬�ǂ�Сƿ��Ҳ�S�뺣�h�������磬��ͬ�҂��ׂ��������E���İ㣬��Ҳ���ܾ͔R��ڸ���ij���ط���Ҳ�]�߳�ȥ��������@���ط��_�l�ɡ�Ұɽ�¡����[���c����ɽ�˺��r���ǂ�Сƿ��Ҳ�S�����h���ڵص����ˡ�
�M���ʮ����������˶�ȥ�x�о����ˣ��е��˄t�M���̽磬��üt�t��𣬴��������څ�������㣬������q�����ѽ��]�����p�r�ǷN���v�Ąŵ��ˡ�ͬ�r���@���r��ÿ���˵���ض�׃�úܴ��ˣ��������ǂ��ط��u�uֻʣ��ӛ��������ͽ��O�����ԳɼҰ��ȥס���҂�����ĕr����ȥ���TҊ������ĸ���Еr���k��·�^�����Mȥ���s�Ͽ����ĕr��ĸ���ó���ë�X�ҵ�����ĸ�ʳ���Iһ�K�i�⣬��r���Ѱ��I�ͺã����˰ײˣ��ܿ���ӾͰ����ˡ��ҳ��˾ͻ�ȥ�ˣ��������Լ�ĸ�H�ǃ�һ�ӡ����������λ�����·��ӣ���e�Դ��@���·��xԭ�ȵ��f�ӁK���h������ͬһС�^�ȣ����ط�׃�����ˣ���Ҷ��ܸ��d����ҵĕr���҂���ȥ�ˣ���ĸ�҂�ȥ�ĕr��혱��ږ|���I�˴���Ƥ�ӣ�������ը�˴�����ҳԡ��ػ����҂��������ģ�������������ʹ����Ů�˵��£�ӛ������̫̫�ͽ�������ý�����؟����̫̫ӛ�Ã�����һֱ��ҹ�eæ��������
�@���r��Ҷ�����æ�Լ����Iȥ�ˡ�ӡ���У�����һ���˶�ۼ��ǰ�����ć��c��醱����������x�찲�T������ĸ���ȥ�ǃ��^�������Ͼͽ��������@�r��Ҷ����ϼҎ��ڵ��ˣ��҂���D���˃��ӡ��˺ܶ࣬��ƽ��ʒ�Y���ѳ���������߀���־����D�������ӡ��@�����^����ǿ��ҕ�D����醱�������һ���߳����DZ���W�������Сƽ���á��ęM������Ҷ��е����r��һ�N�������˺͡��Ě�ա������҂��@Щ������Ҋ��һ���߳�����Ҳ��һ���K�Y���������l����׃��ÿ���˵����Ҳ������ͬ�����ڲ�ͬ��·���ϣ�Ҳ�����˲�ͬ�Ĺ��¡�
����������һ�N�Ļ����Ǯ�����N���˼���M���nײ��ĥ�ϵ�һ���sӰ����һ����������������ڵ��������B�����ϣ��S���������D���^���У������^�����������Ǵ�W���c����M���nײ�ĬF��һ����������������M��������������͕������������nײ�������K��현ݼ{�뵽���������R���О�܉���С��@�NҎ��߀����һ���ձ����x�ġ��ͽ�����f���������ĵܵܽ��O��������������^���������ͅ��x�˴���������飬���о������I����r���������韩���f�������ڱ�����Ҫ���䵽��ء�������@����rͨ�^���������Ϸ�ӳ���R��谵�֪������⣬�f�@�N�O��Ė|���������Ɖ��҂������깤�������������r��һ�������D�_�o��ҫ������_��ȥ�ᣬ��ҫ�������_��ʾ��Ҫ��������M���������I���䡣��������˶����ڱ��������н��鱻���䵽���H�P�S�WԺ�ν̡����r�о������٣��������֎������������W�҅Ǵ������ڣ������������ԌWУ�������Ɍ�ؐ��һ��ȥ�������ڡ����罛����Փ���@�T�n�̡�����R��谵��P�I���ֺ���������������ڇ������L��ˮ���Iһֱ̎���d���С�������{�����Ҍ�Ӌ������Ȼ�ᱻ�Ԫ���У��{�������_�l�y�е��о�Ժ�����ո�Ժ�L���ֹ�����Ȼ���ֵ����������WԺ�ν̄��L�����������ġ����罛��Փ�V�������T���������c�ǵ��Ͱlչ��·���ڌW�g��dz���Ӱ푡�2021���R���ȥ���ᣬ�������ԡ�ӛһλ������������ϵ��R��˼���x�ߡ����}�ļo��e��ӛ�����R��谓��������������L�r��������������v��һ��Ԓ�������ǣ�һ��Ҫ�_�T��ĸ�����R��˼���x���Ǐć�������Ć���R��˼���xʹ�҂�����ҕ�Ї���ǧ��vʷ���۹⣬��t�҂�߀�Ǹij��Q����˼�롣�Ї��ĸĸ��^�����R��˼���x�Ї������^�̣�Ҳ���ٴΏ����烞���Ļ��м�ȡ�I�B���^�̡���ԓ�f�����R���˼�댦�����Ӱ푣����Կ�����ʮ����߳�����һ�����꣬��u�����Tȥ�����Ļ��������ı������@��һ����Ҏ���ԵĹ��ࡣ
�ҳ���ǰϦ����һ��Ҋ�����飬�Dž������߄���һ�����y�Ļ�����ӑ�������c�����⽻�WԺ���ǴΕ��h�����ߵ���V����Ҋ�҂�����Ľ���ӛ�߰��SҲȥ�ˡ�������������ӛ�ߣ����r���S�������������ɞ顸���������W�ҡ������_һ�v�Լ�˽�˵�����С��܇������һ��Ůӛ�ߡ�����������ϣ�ҲҊ���˾��`���푛�|����ϧ�����˶࣬�r�g�־o���҂�����ֻ��ɵЦЦ���]�ܼ�Մ���@�r�����ѽ����F���W�ᣬ���y�Ļ��ᣬһЩԭ�ȟ������ε����Ѷ���ͬ�̶Ȓ����Ļ��ᳱ�С����ã���ȥ�˼��ô��ܿ�Ҳ�����Ļ��@һ�K�����k�����顶�Ļ��Ї����ČW�g�ڿ���һֱŪ�����죬�L�_��ʮ���ꡣ�Еr���룬�ğ�Ѫ�����M���������g����������Ҫ���D׃�����D���Ļ���̽��������@�����ǻش���ǰһֱ��Ū���������}����Ҫ���c���Թ��ԁ����L�����������������£����еġ������Ǻ��P�I�ġ��Ļ�����Ĺ����_ʼ���e��������ˣ��������º����е�·�������϶��c�@�����Һ��@�����������vʷ�����Ĭ����
������IJ�����ĸȥ�������ˣ�������Ё���������Ҳ����Ҋ�棬ÿ���˶���æ�Լ����¡������o�ᣬ�؇�������ͬ����Ҋ�^�״Σ��҂����˕����������һ�ؑ�������˺��¡��Ƕ��ǹ��£���Ҳ���ǚvʷ���F�ڻ��^�����ǘ�һ��������϶���ֹ���҂�����a���ஔһ���ˣ����в�ͬ����ƻ�����Ĺ��£���ϣ������Ҳ��һ�£������҂���δ����մ������Լ���һЩӛ���c���˷�����Ҳ�o�vʷ����һЩ��Ƭ��
����ӛ��ƽ����ϲӛ䛣�������ʰ�����H�{ӛ���������ˬ��£����Lj�ʷ���������������r�g�ͼ����������e©����Щ���飬���c��Ҋ�C��ͬ�о���ӛ�����Ѳ��٣��gӭָ�e�Kӆ����������ʽ�ɼ��r�������塣�x�x��
ZT�����������
��������ʰ��֮ʮһ
���ߣ��l�]��ҹ
����������������һ�N�Ļ����Ǯ�����N���˼���M���nײ��ĥ�ϵ�һ���sӰ����һ����������������ڵ��������B���Թ��ԁ����L�����������������£����еġ������Ǻ��P�I�ġ��Ļ�����Ĺ����_ʼ���e��������ˣ��������º����е�·�������϶��c�@�����Һ��@�����������vʷ�����Ĭ�������ԣ��Ƕ��ǹ��£���Ҳ���ǚvʷ��
�ڴ�ǰ�Ļؑ������e���״��ᵽ�����������@���ط��������н�������֣�Ҳ�ᵽ���ĸ��H��ĸ�H�����䌍�@һ�ҵĹ��£��h���ь�����Ҫ���ʺ��S���ܶࡣ���Գ��ˌ��T��һƪ�⣬��t�����^�a�ġ�
���������ڱ���ı��F��r�J�R�����ѣ��䌍�K��ֹ춹����������ǰl�F�˃��ˌ��r��������Ĺ�ͬ�������ڮ��r��춡���Ѫ���һ����һֱ����һ���f�����в�ͬ�汾������˼����һ�ӣ��fһ���������p�r������������ɻ��M���ӣ�����һ���]����֪���ˣ������˳���������������֮�ᣬ������D���ػ���Ȼ�����ɣ�����һ���]�����Ե��ˡ��F���҂������m�ϣ������Ҍ��Լ���˼���M���w��Փ�������p�r��Щ���£��F�ڻ�������s���¾�����ˡ�
���鸸ĸ�ļ��ڱ���������һ�������ڱ���·������·�ཻ̎����������ǰ�T꣬��ʮ��������ǂ����ӣ�겻�h��ԭ�����fַ��������ǡ������Ո��磬�����Ҿ�������Ę�Ⱥ�e������ĸ��H�н��R�£�ĸ�H���R־���������Բ���ĸ�Q֮�����������ڡ����k�������c����ġ�ʒǬ�ȹ��^�¡��ĸ��С���ͣ��������ijɡ��Ї�ؔ�Q���F�����Ո�ǰ�����������������ǰ݅����ԓ�f������@һ�c���������c�@����ͥ�ߵ����N����ԭ�������������ČW���棬�Һ���ՄՓ��Ԓ�}�h�Ƚ���ࡣ�Еr��ĸ�����Լ���ĸ�H�Ӂ�������ס������Ҳ�ǘOӑ��ϲ�g���@���ƺ����]�Ļ��������˺��҂��@Щ���^�����Ļ������˽�������Մ���g������һ��ԭ�����ϣ��к������ǷN����ͼ�������ԡ�����ҁ������^�࣬������ڱ����r��ס�������ң����ԱȄe�˸�����ij�N�Кw���H�С�
���ҵط��K�������ǷNһ��һ�d�āѾ֣��͏d�eҲ����һ���������g�Ǻ�խ�M�ģ����҂��@Щ�������ѡ��M���ᣬ�ǷN�o�εĿ��g�s�Ǻ����յġ���Ҷ���ˣ��Ƥ�ӵģ�����ĸҪؓ؟���N�ŷ����Еr߀Ҫ�����ĸ���������ӵ����Ѻÿͣ����܇�����Ҳ�ܟ��ĺ��w�N����������һ���Ŵ�ĺڰ��ҕ�C�����r߀����ϣ��֮��Еr���Ϻù�Ŀ����ĸ��ȥ�܇�����һһ���к�����Ո��ҁ����ҕ��
���_ʼ�r������ҁ����ģ�������q����һ�c�����ѣ���Ҫ�Dz���ĸ���R�����Ѻ������춲���һֱ���������������������Ҷ������ČW���Ӱ����ՄՓԒ�}��������֪����m���ǣ�����һЩ����֪���ͬ�W���ѣ�Ȼ�����ͳ��F���ϴ�W�ĸ������ѡ���ʮ������ڣ���ž���1974����1975�����ң��������ҵ����߀�Ǻ܉��ֵģ��˂�ՄՓ�Ķ���С����Ϣ��Ҳ������ʲ�N��1976������_ʼ��׃�������Ǵ����ˎ��ᣬ���������¼����F�������֏߿����@���ط�������Ҋ�C�Ї��ĸ��_�ŵĺ�������@���ط��ͳ��F�˟�Ѫ�������Ӱ���dz����[����ͬ���ˎ�����ͬ����Ϣ���ֳ����ǂ������Ϣ�����ąR���c�����Ǖr��������վ���Щ���Һ��d�^�ˡ�������S�����ѣ��Ҿ������@���r���J�R�ġ���춲����cʒǬ���^�£�����Ҳ�࣬���ă���ʒ�Y���r�ڽ�����ꠣ��ؾ��rҲ���������ҡ�ʒ�Y���r�����ֽ�ʒ�F�����L�øߴ���࣬����ʒǬ�cǰ�����ģ�ʒ�Y��ĸ�ǂ�Ӣ���ˣ�����ʒ�YҲ��һ����òͦ�εĘ��ӡ������Ը������ӣ�����Ԋ���l�����҂��@��Ⱥ�e�ǂ����Ӻ��ˡ�������_���ɞ�һ��Ԋ�ˣ��K�ڇ����W�̽��Ї��ČW�������ϛ]���x�_�����е���������܉�E�����ڵ�����߀��һ�����푛�|�ģ� ���־��Ǹߎ��ӵܣ������r�ڙz��Ժ��������춈̷����T����ͬ�҂�����һ��Ҳ��Ҋ���r�������ҵ��������B�ˡ���ԓ�v�����r�҂��@Щ�˵�˼��߀�����������ǻ�y�ģ��]���ܵ���Ҏ�ČW�g������������̫�t�������ϵ�����˼�������Ǒ{���ǰ�����x���Ы@�������`�еġ��c������푛�|��һ��Մ�r�����e�����á����a�h���ԡ����Ǿ䡸���˟o����������ԡ����r��ץ�A���Y����������Ҷ���һ�N����Ҫ��ץ������ʂ䡣�ҳ���һ�����⣬�����ゃ����������ȥ�ˣ���������ϳ�ȥ�Ҿ��鹲�a�h���[�����ڝ����R�e�@�����ɞ�һ�����x헡���
�@��Ⱥ�w��߀��һЩ�c�����ڱ��F�B꠵ı���֪�����ѣ�����һ�����B�꣬���P�S�����еģ������ϳ��˽����ڮ��r����������֡���һ����ȥ����������æ����n�����B��ȥ��վ����վ�r�����e����һ�����µġ��Y��Փ����һҊ����f���@�����Y��Փ���İ汾�DZ��^�õģ�ֵ�úúÿ��������B���@�r�ѽ����ҕ�C�S�����ˣ���֪��������һ��ϲ�g�x�����ˣ���Ҳ�W���ǂ����ӣ�ȥ�I��һ���°�ġ��Y��Փ�������ϣ�����Լ������]�Еr�g������ͨ�x�^һ�顶�Y��Փ��������B��Ҳδ�ؕ��������x�^�����鮔�r���x����ϵ�������Y��Փ����ԓ�Ǻܾ�ͨ�ģ���Ӌ���B��������Ӱ푣�����һ�������Y��Փ���汾�ĸ�Փ���F�ڿ����҂��@Щ�˶��в���������ŵĺ�Ц���顣
ͬ�r������ĵܵܽ��O����ʯ��ɽ�l늏S�����������܇�Ҳ��Ⱥ��һЩ�ˣ��ЕrҲ������������S�������ֶ�ӛ�����ˣ�ֻӛ�������ҡ���־�ʵȡ���ʮ�����һ��ؚ�F�ͅT����������Ǖrȥ�����ҵ������ˣ����Ά��ǸF���ӣ������ǡ������¡��ĺ��ӣ�һ�㶼�ǃ��ֿտ�ֻ��һ����ȥ���Ǐ�����fԒ�ͳԖ|��������r������ĸ���ϰ࣬�҂��@Щ���ĵ���������I�ˣ��͕�����ȥ�������^�Iһ���賴����Ҷ����̻��ʒ��M���ӡ�����ǰ���ٳ��^�������@�N��������С��Ӳ�������dzԵ������Ӱl�ۡ���Щ����ȥ���˶࣬���@�[����Ҫ��ģ���Dz�ĸ���°�����Ҫæµιʳ�@�����������ġ��P�ć�����ߡ���С�ӂ����Еr�ĵ���ҹ�������qδ�M����ĸ�͕�����S�����˯���ǃ���ӛ����һ������r��ʮ�킀��˯���ǃ����@Ҳ��һ�����^��
�Ǖr�ڽ���Ҹ�Մ�Փ�����rՄՓ���ľ��LJ��ҵ���������Ԟ鶼�ǿ��Ծ����µ��ˣ����Ҷ��Ƿdz��������ģ��ܿɐۣ�Ҳ�ܿ�Ц���Ă�������ٲ������҂��@�ӵ��ˡ��@Щ�����g���е�ֱ�Ӆ��c�˵����ܶ���������߄ӣ����@���r�ڵ������ˎ�ǰ�ᣬ�ǻ������@���ط���ӵĕr�⡣���Ǿ��µĖ|��̽�H���������Ϻ�ȥ���Ǖr��ȫ������ë�ɖ|���Ά��ڄ��^������hՓ�^�քݕ��l��׃�������K�]���뵽���ܿ졣���Ϻ��ᣬ�����ʮ��ʮ�����ң��ӵ�������ţ���ʾ����������׃�����ˎ��ѽ���̨���@�r�Ϻ������]�Є��o��ֱ���������R·�ϲų��F���ֈ�һ���µĕr�����@�NͻȻ���R�ˡ�
�������ٵ�����������׃�ø��ӟ��[������һЩ�����ѣ����ǻ��ཻ�Q���NС����Ϣ���������µģ������ĺ�����M�������P���ˎ͵IJ��Ϻ͈�����Ǖr�������}ӡ�C��Ҳ��֪����Һ��ğ�������ڣ����ֹ�����һ�һ퓳���������һ������Ҳ���O����ɢ�_�����^�������@�N�ֳ����О�����Ǐ��ĸ����������ġ���Щ����������Ϣ���^�ʴ_�K�õ���C�����������Ϣ����ʮ�����š���ʹ�������������Ϣ�Kδ��C����Ҍ�����Ȼ������ʡ�����Լ��M�����W�о�������ӛ���@�䌍Ҳ��ԓ��һ�����о��Ă�������W�n�}��
���ǣ����ܴ������ˎͣ������O��ľք�߀δŤ�D�����r������Ȼ̎��һ��ʮ��·�ڡ����ږ|���o�����c�������ѵĻ�ӣ���һֱ�����j�����rҲ��ֻ��ͨ�^�ż�������ӛ�î����Լ�����һƪ��Փ���¼Ľo���飬��Ӌ���ŷ�̫���]�ֲ�z�l�F���@���dz����ˡ����r���������ڱ���Ҳ�M����һЩ���O��Ļ�ӣ����磬��ͻ�����ַ��N��Ҫ��ĸ��_�ŵĴ��ֈ��f�DZ����������������ġ���֮���҂���������˼��ʂ䣬�ǂ��������Һ���Ҳ�����N�����O�z��Ҳ�S���ܶ���Ѫ�ⷽ���ּ��ϛ]�м���֮�ۡ����������˼ZƱ���X�o���飬�fһ���°lȥ�����ҹ��a�h�����[��ꠡ�
���ǣ��҂������ĵ�����K�]�г��F�F�����һ���ώֲ��ďͳ���ȫ���Ҫ��ĸ��_���γɹ��R���O��·���_ʼ�õ�Ť�D�K���������������ĸ�׃��ʹԭ���҂����еē��Ķ�һ����ȥ�ˡ��@���r��Ҷ�ͬ�@������һ�ӣ����F��һ�N�g������ľ�����ò���������@���ҵ��ֶ���һЩ�����������x�о��������ѡ�����һ���к�ƽ���Ĵ��ˣ��DZ����܌Wϵ���о������@��ȫ��һ����˼������ȫ������ČW�ߣ��mȻֻ�njW������˼���Ć��}������h��һ��ͬW��֮�ϡ���ƽ�F�������~�s���ӣ����ƺ�ՄՓ���Ά��}�^�࣬�����J������������һ���܌W�ҵĶ�λ����ԓ���҂��@��Ⱥ�w�e�ġ��W����ʽ���߀��һ�����w���������ˣ��DZ����ρ�ϵ���о�����������ρ��о��ķ������Z�W����С�Z�N�����ģ����Ժ�ʹ��Ҳ��������Ҳ�ԌW��Ӣ�Z���@������đ�Ӻܴ��˶�����Ӣ�Z�����Ŀ��Z�C������ʹ�Լ��~�������࣬Ҳǧ����Ӌȥ��ȡ�o��̓��η��g��һ�_ʼ��Ȼ�����e��ЦԒ�����r�gһ�L���e�g�������٣�����������Ǡt�����ˡ��@�N�����dz����˚J�塣�F�����������Ĵ�W�e�����Ї����}�Č��ҡ�
��������Ǖr�ѽ��γ���һ����Ӱ�����Ȧ�ӡ����r����������Ⱥ�w����F�����@�N��Ȧ�ӣ������N�ׂ������Ҳ�ܻ�����Ϥ�K������һ�µ��Єӣ���Ҫ�����Ƅ���Сƽ���³����������빤����1978���°��꣬����늈�����߅��·�ڳ��F�ˌ��T���N���ֈ�Ľ֠����@��������ȫ����ע�⡣���r���ږ|���ăȅ��e֪���@���£�ͬ�r�̨�ֲ��l����Сƽ��Ҋ�ձ������hί�T�L����ľ���r�l����ՄԒ���϶����@Щ���ֈ��ҷ��������á��@�r������o�ҁ��ţ�Մ�����ڲ߄�һ����ӡ����������ږ|���o�����c��ֻ��Մ���Լ�һЩ�O�롣�������˼��������k���������꡷�ǷN���|�Ŀ����ĸ���_�ŅȺ����@�ݿ����������r�����顶�������������|����һ���C�Ͽ������Փ���£����u������ˇ��Ʒ�ȡ�����������������c���к�ƽ���w�������푛�|�����ҡ����O��ʒ�Y����ɽ����֮�ʵȡ�
���꣬��늈�����߅�Ƕ ��l�е���ӡ������ˡ��������⣬߀�С����졷������Փ������̽����������֮�����ȣ�����@Щ������Ҫƫ�ؕr�����ٔ����ČW��Ԋ�裬������������һ���C���ԵĿ�����^���f����ߌW�g�L����һ�����oՓ����Փ����߀����ˇ��Ʒ�������ϳ˵���Ʒ������̖���з����Ĵ���������ƪ���Ѓ�ƪ�ǽ����Խ���ĹP�����ģ�һƪՓ�Y�����x��������x�^�ɣ�һƪՓ������x�Ć��}��߀��һƪ�Ǻ�ƽ������L�ġ�Փ��Փ���ɡ����@ƪ����ֱ��Ŀǰ��Ȼ�����ΌW���܌W�I���e���W����ҕ�����õġ�߀��һƪ���푛�|�������Ӱ�ČW������������n���e�����@�������������ܴ�푡������e��Ҳ�B�M���҂��Լ���˼���}�j�������Ǿ䡸���˟o��������Լ���������[�����鹝�����Ǯ����҂�������r������ĵ�˼�롣�푛�|���@���������ںܶ̕r�g���s�����ģ���ȫ�nj��Iˮƽ���f�����dz��Є������x���@�����Ϸ�ӳ�˻������@���c���ˆT�����w���|���ڶ��꣬�ɱ����Ӱ�uƬ�S�����ͳ���ġ��Ӱ������ȫ�Ŀ��l��������n���e�����K�����ĔzӋ����ֻ�����Kδ�ijɡ�
�������@Щ���ꮔ�r��Ӱ푣������������ע�����ҕ�������@Щ����Щ�������ģ����c���r������������ȫ���ģ����Ϯ��r�ߌӸĸ��ɵ�˼·�ͷ�����Ҳ���������ע����P�ա��������������ᣬ����ͨ�^�F�����λ�ֲ������j���������ӛ�������r��ҫ����f���ͺ��������@Щ���g����ӡ�������ҕ�����Õr�ΈF�����о��������R����c�������j���{�У��R���ָ���x����������꿡����������c�����j���K�H�Ե��T���������ľ�������Ҷ�Մ�ú���Ǣ�������˻�ȥ���һ�݈�棬�C�Ϸ����ˮ��r���F��������ӡ������Ќ������������u�r���^���棬�J���ˆT���|ͬ�����ױ���������ǡ������ۺģ��@�����������������ġ��R������߀�Ϊ���Ҋ�˽��飬�ɞ�oԒ��Մ�����꽻�����ã��R��谸������뾫������к����@�N��ӡ���ﲻ�����k��ȥ������Ҳ�����ֹͣ�˿����������@�N�όӺͻ��ӵ����Ի��ӣ��F�ڿ���߀���п�Ȧ���c֮̎�ġ�
�ڱ������g���ҽ��v�ˡ������������ڣ����������^��늈�����߅�ɰl�������Ƿ���ۣ����ÿ����ؓ؟һ���̿�����أ����ۣ�����ȫ����������ֿտգ�Ҳ��һ�N�ɾС���춽���ҁK�����������Ծ����O������һλ����̎����һ��Ͳ�Әǣ��܇����Ǹ������ӣ��M�M�������е��Пo���p�۾����Pע����Һ���Ҳ�����N���¡���ӡ���������������ڱ������M�еģ�ӡ�����Еr�����ҌW���俼���ǂ����g��Ҳ���ǡ�һ���߾��꡷��ƪ���������f��ɽ�����ᡣ�@�e��һ������Ȥ�IJ��������Q�������k���������ᣬ�Ǽ���ӡ�C���̎���ͳ��ˆ��}����ӡ�C�Ǐ�У��һλ���ѽ���ģ���У���õ�У�Ȇ��}�������T�l���ܣ�����У�������ã��T�l�϶�Ҫ�܁K��Ҫ���C���@�ͺ��y���f������ˡ����r�����������M����Ҫ���ږ|���T�����ڱ�߅߀��һ��С�T�������_������վ�������Ͼ����F�T�P�ϡ��Y�����҂��x��һ�����ϣ����F�T�P���ᣬ�ɂ�������ӑ����ɂ������e�������F�T�����@�Ӱ���ӡ�C�D�f�˳�ȥ��ģ��ȫȻ�����һ�ӣ��F������Ҳ��ͦ�����Ϳ�Ц�ġ��䌍������һ���e���������ƬF�������˿����ǻ��Q���x������飬߀�Ǻܶ�ġ�
�o�ɣ��ڻ������ǂ��Ҿۼ�Ȼ�����߳��������ˣ������f�����ǡ�ʡ�͵ğ������������y���f����������һ�����_ʼ�ĸ���_�ŵ���������͇�ÿһ���}�������ӣ����� ������������������1979��֮�ᣬ�mȻ��ӡ�����Dz����k�ˣ����@�����Һ���������ʼ�K�����o�p���ڶ���ͳ��F�˶�����W�ČW�����ӵط���������x�e�ĬF����ĵܵܽ��O�����������W�x�о�������һ���ڴ�ʳ��������g�������������Ұl�����f���K���х��x�˴�������ɞ鮔�r��У��һ�t��Մ������ƽҲ�ڱ�����W���х��x�˴�����������dzɹ����x�������֪��ʲ�N�]��Ϣ�ˡ�
�@Щ���鶼�����w����l���ģ����}�ǣ����Ї����r����r�£�����ܼ{���w�ƃȲ����ܷ������ɹ����P�I���oՓ��Σ��@Щ�˟��ԡ����v���ĕr���Ƕ�ʮ���q������r�ڣ��o����֮�ۣ����]�����֮�n�����ܿ죬���Մ�ِ۵�Մ�ِۣ��ɼҵijɼң��^һ���꣬��������̽�L�ģ������˃�Ů�����Ҳ���߀�������ڸ�Մ�Փ���Ҵ��º������d�������s���ˋ냺�Ŀ�����Ӗ�⺢ͯ�ĺ����ѽ��ǟ��[�Ƿ��������Ͳ�ĸҲ��æ�ò����������@���r�����˼��ҵ��ˣ��ľ����О�ģʽ���l����ijЩ׃�����҂������l�Fһ���F���Ǹ�λ��ӑ�����ţ�����ϲ��f���������e����̫ד���ɷ���ȥ�������λ�ӣ���Ҍ��@һ�cҲδ�γɷ��磬�����Ӽ��^���Ӳ�����Ҫ�ġ�����Ҫ���ǣ��@�r���Һ�����lչ��������һ�N����܉�����҂��е��S���˶��M���w�ƃȹ������@�e�����S��Ҏ�غ���Ҳ�DZ���挦��һ���F����
�ڴ�֮ǰ���������ǂ��ط������ѣ�����һֱ�����ں��Ӱ������֮�С�����������һ�����������@���r���ƺ������D�͕r�̣���ԓ��ij�N��ʽ�ġ����˶Y��������������ijЩ�r���e�и�eʽ�����r�K�]��ʲ�N�˿����뵽�@һ�c�����ǣ������{��һ�½�����ʽ����������@Щ�������ڡ�������ͣ�k�Ἧ�w���[ȥ��һ�η�ɽ�h��ʮ�ɣ��ھ��R���ϴ���һ�졣
�����҂����������T��վ�����ϵĻ�܇�����˽�����ޡ����O�ȣ�������͡��������ġ������ѡ��ֶ����ˣ�������ƽ��ʒ�Y���w���������B��ȣ���Ҷ����˳Եģ����������ε�Ұ�͡��@���ط����r��δ�_�l���[�YԴ��һ�ж���ԭ���B������ؚ�F�������ԭ���B����������Ǜ]����ՄՓ���Ҵ��£������档�Һͽ���ķ�����һ�Ԍ�����u��ʯ�K���ʂ���o���Ū�ڟᜫ��ֻ�����ț]��֪ͨ�y�I�������|������ȱ��ȼ���ľ��Ҳ�]��ú�͡���ǽ������Һ�һ���ˣ���ӛ���l�ˣ��ܿ����DŽ��B�꣩��ȥ�����r��ӑҪЩľ���ú�͡��҂��������M���f��Ҳ�S����æ�r����e�˺��٣�����Ҳ�]�P�T�����������ؼҡ������@���ط����x���DzŎ�ʮ����ʶ��������_�£���������͚������Ҹе�һ�N�Թ��ԁ���ؚ�F�����ᣬ�@Щ�|�������҂��ڳ��e��Մ�Փ�r�o�����ġ��@�����������һֱ�]�В{ȥ�����е��@��������̝Ƿ���S���˵ġ�
�Ǖr���|�T������Ҏ���ʳ�ﶼ�ܺ��Σ���߀����ĺܱM�ԣ���һ����������C�������ܴF���dz��П��[�С�����һ���߳��ǣ����O�ü����ˎ�Ԓ��������ʲ�N������һ��Сƿ�Ӄȣ�Ȼ��[��һ���f�xʽ�Ę��ӣ�ͬʒ�Y��������ѝ�ܣ�����������R���С�ʒ�Y��Сƿ���e�^�^�����O�t��������C���������ط���ؐ��ҵĵ��彻푘�������ߡ�����Ȼ���������µ��ں����İ��ǂ�Сƿ�ӷ���ˮ��Ư�ߡ����r����ڰ�߅��Ц���@һĻ�ģ������Ǹ����Ӻ���ͬ�������������đB��һ�ӣ�����߀��һЩ�J���ģ�ӣ��@������ӛ�����h�ġ����R��������ȥ�Ǵ���ӣ�Ȼ����R�뺣�ӣ�������������������룬�ǂ�Сƿ��Ҳ�S�뺣�h�������磬��ͬ�҂��ׂ��������E���İ㣬��Ҳ���ܾ͔R��ڸ���ij���ط���Ҳ�]�߳�ȥ��������@���ط��_�l�ɡ�Ұɽ�¡����[���c����ɽ�˺��r���ǂ�Сƿ��Ҳ�S�����h���ڵص����ˡ�
�M���ʮ����������˶�ȥ�x�о����ˣ��е��˄t�M���̽磬��üt�t��𣬴��������څ�������㣬������q�����ѽ��]�����p�r�ǷN���v�Ąŵ��ˡ�ͬ�r���@���r��ÿ���˵���ض�׃�úܴ��ˣ��������ǂ��ط��u�uֻʣ��ӛ��������ͽ��O�����ԳɼҰ��ȥס���҂�����ĕr����ȥ���TҊ������ĸ���Еr���k��·�^�����Mȥ���s�Ͽ����ĕr��ĸ���ó���ë�X�ҵ�����ĸ�ʳ���Iһ�K�i�⣬��r���Ѱ��I�ͺã����˰ײˣ��ܿ���ӾͰ����ˡ��ҳ��˾ͻ�ȥ�ˣ��������Լ�ĸ�H�ǃ�һ�ӡ����������λ�����·��ӣ���e�Դ��@���·��xԭ�ȵ��f�ӁK���h������ͬһС�^�ȣ����ط�׃�����ˣ���Ҷ��ܸ��d����ҵĕr���҂���ȥ�ˣ���ĸ�҂�ȥ�ĕr��혱��ږ|���I�˴���Ƥ�ӣ�������ը�˴�����ҳԡ��ػ����҂��������ģ�������������ʹ����Ů�˵��£�ӛ������̫̫�ͽ�������ý�����؟����̫̫ӛ�Ã�����һֱ��ҹ�eæ��������
�@���r��Ҷ�����æ�Լ����Iȥ�ˡ�ӡ���У�����һ���˶�ۼ��ǰ�����ć��c��醱����������x�찲�T������ĸ���ȥ�ǃ��^�������Ͼͽ��������@�r��Ҷ����ϼҎ��ڵ��ˣ��҂���D���˃��ӡ��˺ܶ࣬��ƽ��ʒ�Y���ѳ���������߀���־����D�������ӡ��@�����^����ǿ��ҕ�D����醱�������һ���߳����DZ���W�������Сƽ���á��ęM������Ҷ��е����r��һ�N�������˺͡��Ě�ա������҂��@Щ������Ҋ��һ���߳�����Ҳ��һ���K�Y���������l����׃��ÿ���˵����Ҳ������ͬ�����ڲ�ͬ��·���ϣ�Ҳ�����˲�ͬ�Ĺ��¡�
����������һ�N�Ļ����Ǯ�����N���˼���M���nײ��ĥ�ϵ�һ���sӰ����һ����������������ڵ��������B�����ϣ��S���������D���^���У������^�����������Ǵ�W���c����M���nײ�ĬF��һ����������������M��������������͕������������nײ�������K��현ݼ{�뵽���������R���О�܉���С��@�NҎ��߀����һ���ձ����x�ġ��ͽ�����f���������ĵܵܽ��O��������������^���������ͅ��x�˴���������飬���о������I����r���������韩���f�������ڱ�����Ҫ���䵽��ء�������@����rͨ�^���������Ϸ�ӳ���R��谵�֪������⣬�f�@�N�O��Ė|���������Ɖ��҂������깤�������������r��һ�������D�_�o��ҫ������_��ȥ�ᣬ��ҫ�������_��ʾ��Ҫ��������M���������I���䡣��������˶����ڱ��������н��鱻���䵽���H�P�S�WԺ�ν̡����r�о������٣��������֎������������W�҅Ǵ������ڣ������������ԌWУ�������Ɍ�ؐ��һ��ȥ�������ڡ����罛����Փ���@�T�n�̡�����R��谵��P�I���ֺ���������������ڇ������L��ˮ���Iһֱ̎���d���С�������{�����Ҍ�Ӌ������Ȼ�ᱻ�Ԫ���У��{�������_�l�y�е��о�Ժ�����ո�Ժ�L���ֹ�����Ȼ���ֵ����������WԺ�ν̄��L�����������ġ����罛��Փ�V�������T���������c�ǵ��Ͱlչ��·���ڌW�g��dz���Ӱ푡�2021���R���ȥ���ᣬ�������ԡ�ӛһλ������������ϵ��R��˼���x�ߡ����}�ļo��e��ӛ�����R��谓��������������L�r��������������v��һ��Ԓ�������ǣ�һ��Ҫ�_�T��ĸ�����R��˼���x���Ǐć�������Ć���R��˼���xʹ�҂�����ҕ�Ї���ǧ��vʷ���۹⣬��t�҂�߀�Ǹij��Q����˼�롣�Ї��ĸĸ��^�����R��˼���x�Ї������^�̣�Ҳ���ٴΏ����烞���Ļ��м�ȡ�I�B���^�̡���ԓ�f�����R���˼�댦�����Ӱ푣����Կ�����ʮ����߳�����һ�����꣬��u�����Tȥ�����Ļ��������ı������@��һ����Ҏ���ԵĹ��ࡣ
�ҳ���ǰϦ����һ��Ҋ�����飬�Dž������߄���һ�����y�Ļ�����ӑ�������c�����⽻�WԺ���ǴΕ��h�����ߵ���V����Ҋ�҂�����Ľ���ӛ�߰��SҲȥ�ˡ�������������ӛ�ߣ����r���S�������������ɞ顸���������W�ҡ������_һ�v�Լ�˽�˵�����С��܇������һ��Ůӛ�ߡ�����������ϣ�ҲҊ���˾��`���푛�|����ϧ�����˶࣬�r�g�־o���҂�����ֻ��ɵЦЦ���]�ܼ�Մ���@�r�����ѽ����F���W�ᣬ���y�Ļ��ᣬһЩԭ�ȟ������ε����Ѷ���ͬ�̶Ȓ����Ļ��ᳱ�С����ã���ȥ�˼��ô��ܿ�Ҳ�����Ļ��@һ�K�����k�����顶�Ļ��Ї����ČW�g�ڿ���һֱŪ�����죬�L�_��ʮ���ꡣ�Еr���룬�ğ�Ѫ�����M���������g����������Ҫ���D׃�����D���Ļ���̽��������@�����ǻش���ǰһֱ��Ū���������}����Ҫ���c���Թ��ԁ����L�����������������£����еġ������Ǻ��P�I�ġ��Ļ�����Ĺ����_ʼ���e��������ˣ��������º����е�·�������϶��c�@�����Һ��@�����������vʷ�����Ĭ����
������IJ�����ĸȥ�������ˣ�������Ё���������Ҳ����Ҋ�棬ÿ���˶���æ�Լ����¡������o�ᣬ�؇�������ͬ����Ҋ�^�״Σ��҂����˕����������һ�ؑ�������˺��¡��Ƕ��ǹ��£���Ҳ���ǚvʷ���F�ڻ��^�����ǘ�һ��������϶���ֹ���҂�����a���ஔһ���ˣ����в�ͬ����ƻ�����Ĺ��£���ϣ������Ҳ��һ�£������҂���δ����մ������Լ���һЩӛ���c���˷�����Ҳ�o�vʷ����һЩ��Ƭ��
����ӛ��ƽ����ϲӛ䛣�������ʰ�����H�{ӛ���������ˬ��£����Lj�ʷ���������������r�g�ͼ����������e©����Щ���飬���c��Ҋ�C��ͬ�о���ӛ�����Ѳ��٣��gӭָ�e�Kӆ����������ʽ�ɼ��r�������塣�x�x��